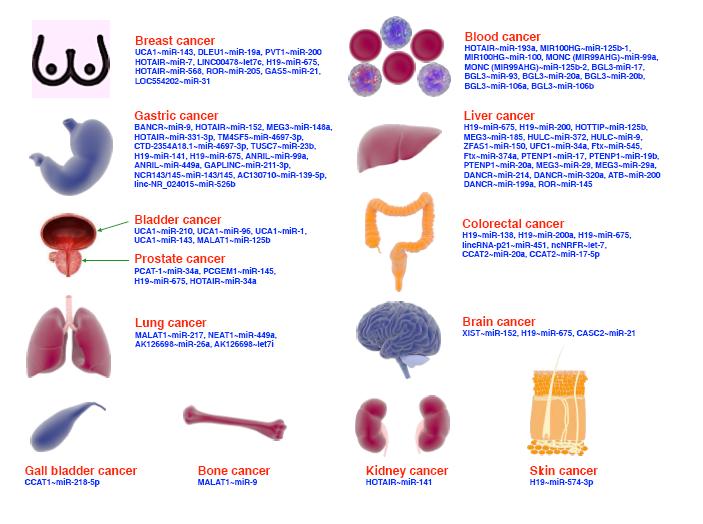癲癇是臨床上最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目前癲癇最常用、最重要的治療手段仍是藥物治療,而耐藥性癲癇的存在成為當前抗癲癇治療的一大難題。現已證明,Wnt/β-連環蛋白通路,作為大腦神經元發生的分子機制,在癲癇的急性期和慢性形成階段均發生紊亂。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參與調節許多癲癇發作誘導的腦內變化,包括神經發生和死亡,從而參與癲癇發作的進展。然而該通路影響神經發生的動態變化及通過靶向干預達到治療目的的具體作用時間仍需進一步研究。總之,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紊亂,可能成為未來有前景的抗癲癇靶點。
引用本文: 王柯黙, 劉學伍. 癲癇發作誘導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的變化—新型抗癲癇治療的潛在靶點. 癲癇雜志, 2019, 5(4): 285-288. doi: 10.7507/2096-0247.20190048 復制
癲癇是由于腦部神經元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引起的以反復發作為特征的疾病,是最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影響全球約 1% ~ 4% 的人口,且與多種認知和神經生物學后果及合并癥發病率的增加有關[1]。目前全世界約有 5 千萬人患有癲癇,30%~40% 的患者使用藥物治療后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癲癇的發病機制十分復雜,至今未完全闡明,這也是臨床治愈率有限的原因[2]。癲癇的發生是多因素的,許多先天性和獲得性機制都可以引起異常腦電活動導致癲癇發作及合并癥的出現[3]。很多癲癇源于大腦興奮-抑制失衡,與離子通道或神經遞質系統的電生理性能失調有關。
有多種治療方法可用于控制癲癇發作,包括藥物和非藥物治療,如迷走神經刺激、手術和飲食療法,其中藥物治療是癲癇臨床治療的主要方法[4]。然而,盡管治療方案多種多樣,但約 1/3 的癲癇患者仍然會出現癲癇發作并且對所有可用的治療方法具有抵抗性[5]。許多藥物治療旨在阻止或減少癲癇發作,但不能解決導致紊亂的潛在機制的異常。因此,許多治療方案通常無法減輕與癲癇發作相關的認知和行為障礙。在過去的十年中,癲癇領域已經開始研究抗癲癇治療的新型機制靶點,旨在對抗這種疾病的根本原因并抑制慢性癲癇的發展。
新型抗癲癇治療的發展很可能針對選擇作用機制的靶點,而不是影響興奮-抑制失衡本身。這種可選靶點可能是分子網絡,這些分子網絡經常在癲癇發作后和慢性癲癇發作中發生紊亂。例如,先前的研究已經證明,在患有遺傳性和獲得性癲癇患者的腦組織及癲癇體內動物模型中,mTOR 信號通路發生失調[6]。現已發現,在小鼠癲癇模型中,mTOR 通路抑制性藥物能拮抗癲癇發作—抑制神經元死亡并減少癲癇發作后誘發的樹突和星形細胞損傷[7]。用雷帕霉素抑制 mTOR 也可以延遲體內癲癇發生,這通常被歸因于苔蘚纖維出芽的減少,但海馬中的其他結構變化也可能會帶來抗癲癇發作效應[8]。臨床研究也發現,mTOR 抑制劑依維莫司是一種雷帕霉素類似物,它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的用于治療結節性硬化綜合征的藥物,并且已顯示可有效降低患者的癲癇發作頻率[9]。
1 Wnt 信號分子及信號通路
Wnt 是由一組分泌性糖蛋白組成的大家族,調控著生物體生長、發育及疾病發生、發展、轉歸等各個方面,在中樞神經系統發育(如細胞增殖、分化、細胞結局、細胞凋亡、軸向激化及神經軸突導向等)和突觸重塑過程中起重要作用[10]。Wnt 信號傳導通路在物種中高度保守,對于正常胚胎和中樞神經系統(CNS)的發育以及在成年期維持組織穩態至關重要。Wnt 作為配體與 G-蛋白偶聯跨膜卷曲蛋白(Fz)受體結合后激活多種不同的信號通路,包括 Wnt/β-連環蛋白途徑、平面細胞極化途徑和“Wnt-鈣離子”途徑。后兩者不依賴于主要效應物分子 β-連環蛋白,因此被稱為“非經典途徑”[11]。本文綜述將主要集中在三者中具特征性的途徑,即經典的 Wnt/β-連環蛋白信號級聯反應,因為這種途徑的破壞更常導致癲癇發病。
經典 Wnt/β-連環蛋白途徑可以被大量分泌性 Wnt 配體激活。這些 Wnt 糖蛋白與細胞表面 Fz 受體及協同活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受體相關蛋白(LRP5 或 LRP6)結合。與 Fz 受體結合引起細胞膜表面復合物的形成,隨后磷酸化,激活下游分子,解聚(Dvl),這將抑制糖原合酶激酶 3(GSK3)的活性。GSK3 活性的抑制將阻止 β-連環蛋白的磷酸化,從而維持其結構穩定并在胞質中積聚、易位至細胞核,通過與 DNA 結合的 TCF/LEF(轉錄因子)激活基因轉錄。
無 Wnt 糖蛋白結合時,β-連環蛋白將被“破壞復合物”(DC)降解,該復合物由支架蛋白 Axin、腫瘤抑制基因 APC、構成性活化絲氨酸-蘇氨酸的酪蛋白激酶 I(CK1)和 GSK3,以及 E3 泛素連接酶 β-TrCP 所組成。β-連環蛋白的氨基末端區域被 CK1 和 GSK3 依次磷酸化,從而被 β-TrCP 識別和泛素化,隨后被蛋白酶體降解。蛋白酶體介導的 β-連環蛋白持續性降解可阻止其進入細胞核并影響靶基因的下游轉錄。在這種無活性狀態下,TCF/LEF 轉錄因子由于阻遏物 Groucho 的結合而失活[12]。因此,經典 Wnt 途徑的復雜性提供了許多潛在的治療靶點,包括 Wnt 配體和 Wnt 拮抗劑的調節,控制 DC 組分水平的酶活性,以及 β-連環蛋白水平的直接調節。
2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與癲癇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的失調涉及許多神經系統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癥、自閉癥譜系障礙、阿爾茨海默病、情緒障礙和癲癇[13, 14]。這種聯系的證據直接源于全基因組研究和體內敲除(KO)動物模型。此外,通過觀察調節 Wnt 活性的治療效果,進一步間接的證明了這一點。研究發現,Wnt 信號通路分子的高表達與癲癇發作后常見的神經發生和神經元死亡的增加有關。此外,通過調節 Wnt 信號通路,缺血和癲癇發作后引起的神經元損傷和死亡將會減少[15]。已有研究發現,拮抗 Wnt 通路的內源性抑制劑,如 Dickkopf-1(Dkk-1),可抑制海馬硬化的發展,而海馬硬化便是顳葉癲癇的標志[16]。然而,盡管已經確定了幾種可以直接影響 Wnt 信號通路的小分子和其他藥物療法,仍鮮有研究探討這些化合物對癲癇發作具體影響的報道。
2.1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與神經發生
有證據表明,Wnt 信號通路及其復雜的調節機制可作為神經發生的關鍵性雙峰調節因子,促進神經元穩態的正負調節。成人大腦的神經干細胞(NSCs)/祖細胞的神經元分化發生在兩個區域,側腦室的腦室下區(SVZ)和海馬齒狀回的亞粒區(SGZ)。幾種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配體(Wnt3、Wnt5a、Wnt7a、Wnt8b)和受體(Fz1、Fz2、Fz9)在 SGZ 中均有表達,它們能夠調節 NSCs 的活動[17]。
有證據表明,單次癲癇發作或損傷可以增加神經發生的速度,而在癲癇的慢性期,神經元發生會大大減少[17]。這在各種體內癲癇發作模型以及癲癇患者死后的腦組織中被大量證明。在癲癇的慢性期中神經發生減少可能會加劇大腦的過度興奮,因為生成的抑制性中間神經元和突觸連接的數量減少。
急性癲癇發作后出現神經發生增強的機制,以及這如何加速慢性癲癇的發展仍存在爭議。在興奮性刺激后的急性期和慢性期都發現了與神經發生相關的幾種分子變化。在急性期,許多生長因子的表達增加,包括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神經生長因子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18]。在慢性期,減少的神經營養因子和干/祖細胞增殖因子以及腦內炎癥的增加與此階段的神經發生減少有關。然而,癲癇發作后協調這些變化的機制仍有待闡明。前文提到許多相關的分子變化可以通過 Wnt/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通路起作用,因為許多 Wnt 信號傳導蛋白在癲癇發作后也急劇升高。
有關 β-連環蛋白在癲癇發作所起作用的前期研究發現,電驚厥性癲癇發作上調了大鼠海馬新生神經元中 β-連環蛋白和 Wnt 2 配體基因表達[19]。升高的 β-連環蛋白定位于齒狀回的亞粒區(SGZ),齒狀回是成年哺乳動物腦中能夠在整個壽命期間產生新神經元的兩個區域之一。Pirone 等[20]研究發現 APC 條件性敲除小鼠(APC cko)神經元內 β-連環蛋白表達水平增加,伴有明顯的多種類型的痙攣發作。另一項研究發現,局灶性皮質缺血后 Wnt/β-連環蛋白信號在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中升高。與野生型(WT)小鼠相比,Catnb 小鼠對戊四氮(PTZ)誘導的癲癇發作易感性增加,包括癲癇/死亡的潛伏期縮短和癲癇發作次數增加,且表現為皮質發育異常[21]。總之,這些研究強調了癲癇動物模型中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在控制癲癇易感性、神經發生和潛在癲癇發生中的重要性。
基因表達研究還強調了嚙齒動物模型中實驗誘導癲癇發作后 Wnt 信號通路的作用。一項基因表達譜分析研究發現,在出生后第 10 天缺氧誘導癲癇發作,12 h 后 Wnt/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組分大量表達,包括 β-連環蛋白(CTNNB1)基因、共受體 LRP6、Fz 配體(WNT2、WNT5A、WNT10 A)和 β-連環蛋白破壞復合物組分(GSK3β、AXIN2、APC)[22]。另一項涉及癲癇相關 microRNA(miRNA)表達和信號通路調控的研究發現,在顳葉癲癇模型(TLE)中,癲癇持續狀態(Status epilepticus,SE)后大鼠 Wnt 信號通路靶基因(Wnt3、Fzd5、Dvl2、Dkk-2)miRNA 顯著上調或下調[23],表明沉默或激活 Wnt 通路靶基因的特定 miRNA 具有治療潛力。
2.2 癲癇患者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靶向治療效果
目前,抗癲癇藥物(AEDs)的機制主要是降低神經元興奮性和調節離子通道功能[提高 γ-氨基丁酸(GABA)能神經傳遞、降低谷氨酸能神經傳遞、抑制電壓門控離子通道和改變細胞內信號轉導通路等][1],以預防或減少大腦的癲癇活動,從而阻止或減少癲癇發作。雖然有多種類型的 AEDs 可用,但約 1/3 的癲癇患者仍對治療產生抵抗,約 30% 的患者存在多藥耐藥(通過至少 3 種合適的 AEDs 足量、足療程治療后癲癇癥狀仍然存在)。針對耐藥癲癇,尋找替代的更有效的治療方法至關重要。
新型抗癲癇治療方案的研究不應該局限于對神經元興奮性和控制失衡的直接作用,而應關注癲癇發作后被破壞的細胞機制。有大量證據表明,癲癇發作后 Wnt/β-連環蛋白活性發生改變且該途徑在調節神經元死亡和神經發生中起作用。因此,該途徑的新靶點可能在未來的癲癇治療中具有重要的治療潛力[24]。干預 Wnt/β-連環蛋白途徑會影響癲癇發作時腦內的潛在分子機制,因此,與現有的 AEDs 相比,能從根本上遏制癲癇電活動的發生及病程的進展。
典型的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可以受到多種不同機制的影響,包括已經獲批準和廣泛應用的藥物,以及許多靶向信號傳導通路的小分子組分。GSK3β 是一種較好的研究靶點,對恢復 Wnt/β-連環蛋白穩態具有良好效果。GSK3β 的抑制阻止了 β-連環蛋白的磷酸化和破壞,從而使得 β-連環蛋白積累并易位進入細胞核以激活下游基因。Busceti 等[25]發現,在臨床實踐中廣泛使用的 GSK3β 抑制劑氯化鋰能在大鼠紅藻氨酸(KA)致癲癇發作后 7 d 保護其免于癲癇發作誘導的海馬神經元損傷。除氯化鋰外,還有許多其他化合物和內源性化學物質可以抑制 GSK3β 活性,從而恢復 Wnt 信號通路的穩定,包括 kenpaullone、SB-216763、L807mts、LY2090314、NPO3112(tideglusib),雌激素和廣泛使用的 AEDs 丙戊酸鈉[11, 26]。研究表明,這些化合物可在各種環境下有效促進神經發生,然而,在體內癲癇模型中直接檢測 GSK3β 抑制對癲癇發作效果的研究仍有限。
調節 Wnt 信號通路活性的另一種潛在機制是 Wnt 途徑的靶向內源性拮抗劑。例如,Dkk-1 通過與共受體 LRP5/6 相互作用選擇性地拮抗 Wnt 信號傳導,從而阻止受體與 Wnt 配體結合。Dkk-1 參與大腦神經元的生理性調節,而其在癲癇灶中的過表達影響正常 Wnt 途徑的穩定。在該 TLE 大鼠模型中神經元死亡前的急性期,KA 誘導癲癇發作后,Dkk-1 表達增加[27]。此外,用反義寡核苷酸敲低 Dkk-1 能夠對抗大鼠癲癇發作誘導的神經元死亡。TLE 患者的海馬組織也顯示出 Dkk-1 高表達,Dkk-1 拮抗劑可能是降低 TLE 相關神經元損傷程度的有益靶標。而雌二醇(E2)在維持 Dkk1 和 Wnt/β 連環蛋白信號傳導的平衡中起到重要作用[27]。除了 Dkk 蛋白外,還有許多其他內源性配體可拮抗 Wnt/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這些可能是恢復 Wnt 信號通路的潛在靶點,包括 Wnt 抑制因子-1(WIF-1)、分泌性卷曲蛋白相關蛋白(sFRPs)、Shisa 蛋白和 Wise/SOST 家族中的蛋白質[28]。
除內源性配體外,還存在多種 Wnt 信號通路的小分子抑制劑,在癲癇發作急性期(Wnt 通路活性通常升高)應用可帶來益處。然而,這些尚未在癲癇模型中進行研究。Axin 是 β-連環蛋白破壞復合物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作為潛在靶點。一些分子,如 XAV939 和 IWR,可抑制端錨聚合酶,這是一種調節 β-連環蛋白破壞復合物中 Axin 穩定性聚合酶。因此,這些化合物(XAV939、IWR)激活并增加 Axin 水平,導致 β-連環蛋白降解增加和 Wnt 靶基因轉錄減少[17]。其他化合物如 IWP2、C59 和 LGK974,具有抑制 Porcupine 的作用。Porcupine 是負責催化 Wnt 配體蛋白酰化的酶。這些分子可能降低 Wnt 配體表達并抑制整個 Wnt 通路的活性[29]。
當抑制癲癇發作后的 Wnt 活性時,Wnt 介導的其他作用也會受到影響。信號傳導對于許多正常細胞過程(如突觸傳遞和可塑性)的調節也非常關鍵。評估癲癇發作后 Wnt 信號傳導降低對認知造成的影響也非常重要,因為抑制 Wnt 活性可損害長期強化并可能對學習和記憶產生不利影響。Wnt 抑制具有神經保護和潛在認知副作用雙重效應,應繼續研究癲癇發作后抑制途徑的最佳時間和方法。
3 展望
綜上,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與癲癇的多個方面密切相關,包括癲癇發作誘導的神經發生、癲癇發作易感性,以及慢性癲癇的潛在發展。然而,研究結果相對有限,并且該通路的組分如何直接或間接介導癲癇發生的機制需要進一步研究。一些研究利用嚙齒動物癲癇模型,檢測癲癇發作后急性和慢性期神經發生。多數研究發現,Wnt 蛋白水平與這些時間段沒有相關性。因此,在癲癇發作和進展的不同階段,該通路影響神經發生的動態變化仍需更多的研究。為了進一步明確在何時、如何干涉該途徑從而使其作為癲癇的治療的靶標最有益,繼續相關研究仍很重要。當在癲癇發作后干預 Wnt 信號傳導時,必須檢測和觀察該干預對 Wnt 介導下游通路的影響。
綜上,目前癲癇治療以藥物為主,而 AEDs 的作用機制一般是對離子通道和神經遞質的影響,很少涉及癲癇發作的分子機制。耐藥性癲癇的存在使得具有分子靶向治療的新型 AEDs 研究成為熱點,這些治療可以使患者潛在性地減少藥物抵抗的可能性,并且有助于減輕癲癇發作相關的認知缺陷。癲癇發作后失調的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和其他細胞信號級聯反應,將有望成為未來抗癲癇治療的選擇靶標。
癲癇是由于腦部神經元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引起的以反復發作為特征的疾病,是最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影響全球約 1% ~ 4% 的人口,且與多種認知和神經生物學后果及合并癥發病率的增加有關[1]。目前全世界約有 5 千萬人患有癲癇,30%~40% 的患者使用藥物治療后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癲癇的發病機制十分復雜,至今未完全闡明,這也是臨床治愈率有限的原因[2]。癲癇的發生是多因素的,許多先天性和獲得性機制都可以引起異常腦電活動導致癲癇發作及合并癥的出現[3]。很多癲癇源于大腦興奮-抑制失衡,與離子通道或神經遞質系統的電生理性能失調有關。
有多種治療方法可用于控制癲癇發作,包括藥物和非藥物治療,如迷走神經刺激、手術和飲食療法,其中藥物治療是癲癇臨床治療的主要方法[4]。然而,盡管治療方案多種多樣,但約 1/3 的癲癇患者仍然會出現癲癇發作并且對所有可用的治療方法具有抵抗性[5]。許多藥物治療旨在阻止或減少癲癇發作,但不能解決導致紊亂的潛在機制的異常。因此,許多治療方案通常無法減輕與癲癇發作相關的認知和行為障礙。在過去的十年中,癲癇領域已經開始研究抗癲癇治療的新型機制靶點,旨在對抗這種疾病的根本原因并抑制慢性癲癇的發展。
新型抗癲癇治療的發展很可能針對選擇作用機制的靶點,而不是影響興奮-抑制失衡本身。這種可選靶點可能是分子網絡,這些分子網絡經常在癲癇發作后和慢性癲癇發作中發生紊亂。例如,先前的研究已經證明,在患有遺傳性和獲得性癲癇患者的腦組織及癲癇體內動物模型中,mTOR 信號通路發生失調[6]。現已發現,在小鼠癲癇模型中,mTOR 通路抑制性藥物能拮抗癲癇發作—抑制神經元死亡并減少癲癇發作后誘發的樹突和星形細胞損傷[7]。用雷帕霉素抑制 mTOR 也可以延遲體內癲癇發生,這通常被歸因于苔蘚纖維出芽的減少,但海馬中的其他結構變化也可能會帶來抗癲癇發作效應[8]。臨床研究也發現,mTOR 抑制劑依維莫司是一種雷帕霉素類似物,它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的用于治療結節性硬化綜合征的藥物,并且已顯示可有效降低患者的癲癇發作頻率[9]。
1 Wnt 信號分子及信號通路
Wnt 是由一組分泌性糖蛋白組成的大家族,調控著生物體生長、發育及疾病發生、發展、轉歸等各個方面,在中樞神經系統發育(如細胞增殖、分化、細胞結局、細胞凋亡、軸向激化及神經軸突導向等)和突觸重塑過程中起重要作用[10]。Wnt 信號傳導通路在物種中高度保守,對于正常胚胎和中樞神經系統(CNS)的發育以及在成年期維持組織穩態至關重要。Wnt 作為配體與 G-蛋白偶聯跨膜卷曲蛋白(Fz)受體結合后激活多種不同的信號通路,包括 Wnt/β-連環蛋白途徑、平面細胞極化途徑和“Wnt-鈣離子”途徑。后兩者不依賴于主要效應物分子 β-連環蛋白,因此被稱為“非經典途徑”[11]。本文綜述將主要集中在三者中具特征性的途徑,即經典的 Wnt/β-連環蛋白信號級聯反應,因為這種途徑的破壞更常導致癲癇發病。
經典 Wnt/β-連環蛋白途徑可以被大量分泌性 Wnt 配體激活。這些 Wnt 糖蛋白與細胞表面 Fz 受體及協同活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受體相關蛋白(LRP5 或 LRP6)結合。與 Fz 受體結合引起細胞膜表面復合物的形成,隨后磷酸化,激活下游分子,解聚(Dvl),這將抑制糖原合酶激酶 3(GSK3)的活性。GSK3 活性的抑制將阻止 β-連環蛋白的磷酸化,從而維持其結構穩定并在胞質中積聚、易位至細胞核,通過與 DNA 結合的 TCF/LEF(轉錄因子)激活基因轉錄。
無 Wnt 糖蛋白結合時,β-連環蛋白將被“破壞復合物”(DC)降解,該復合物由支架蛋白 Axin、腫瘤抑制基因 APC、構成性活化絲氨酸-蘇氨酸的酪蛋白激酶 I(CK1)和 GSK3,以及 E3 泛素連接酶 β-TrCP 所組成。β-連環蛋白的氨基末端區域被 CK1 和 GSK3 依次磷酸化,從而被 β-TrCP 識別和泛素化,隨后被蛋白酶體降解。蛋白酶體介導的 β-連環蛋白持續性降解可阻止其進入細胞核并影響靶基因的下游轉錄。在這種無活性狀態下,TCF/LEF 轉錄因子由于阻遏物 Groucho 的結合而失活[12]。因此,經典 Wnt 途徑的復雜性提供了許多潛在的治療靶點,包括 Wnt 配體和 Wnt 拮抗劑的調節,控制 DC 組分水平的酶活性,以及 β-連環蛋白水平的直接調節。
2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與癲癇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的失調涉及許多神經系統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癥、自閉癥譜系障礙、阿爾茨海默病、情緒障礙和癲癇[13, 14]。這種聯系的證據直接源于全基因組研究和體內敲除(KO)動物模型。此外,通過觀察調節 Wnt 活性的治療效果,進一步間接的證明了這一點。研究發現,Wnt 信號通路分子的高表達與癲癇發作后常見的神經發生和神經元死亡的增加有關。此外,通過調節 Wnt 信號通路,缺血和癲癇發作后引起的神經元損傷和死亡將會減少[15]。已有研究發現,拮抗 Wnt 通路的內源性抑制劑,如 Dickkopf-1(Dkk-1),可抑制海馬硬化的發展,而海馬硬化便是顳葉癲癇的標志[16]。然而,盡管已經確定了幾種可以直接影響 Wnt 信號通路的小分子和其他藥物療法,仍鮮有研究探討這些化合物對癲癇發作具體影響的報道。
2.1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與神經發生
有證據表明,Wnt 信號通路及其復雜的調節機制可作為神經發生的關鍵性雙峰調節因子,促進神經元穩態的正負調節。成人大腦的神經干細胞(NSCs)/祖細胞的神經元分化發生在兩個區域,側腦室的腦室下區(SVZ)和海馬齒狀回的亞粒區(SGZ)。幾種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配體(Wnt3、Wnt5a、Wnt7a、Wnt8b)和受體(Fz1、Fz2、Fz9)在 SGZ 中均有表達,它們能夠調節 NSCs 的活動[17]。
有證據表明,單次癲癇發作或損傷可以增加神經發生的速度,而在癲癇的慢性期,神經元發生會大大減少[17]。這在各種體內癲癇發作模型以及癲癇患者死后的腦組織中被大量證明。在癲癇的慢性期中神經發生減少可能會加劇大腦的過度興奮,因為生成的抑制性中間神經元和突觸連接的數量減少。
急性癲癇發作后出現神經發生增強的機制,以及這如何加速慢性癲癇的發展仍存在爭議。在興奮性刺激后的急性期和慢性期都發現了與神經發生相關的幾種分子變化。在急性期,許多生長因子的表達增加,包括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神經生長因子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18]。在慢性期,減少的神經營養因子和干/祖細胞增殖因子以及腦內炎癥的增加與此階段的神經發生減少有關。然而,癲癇發作后協調這些變化的機制仍有待闡明。前文提到許多相關的分子變化可以通過 Wnt/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通路起作用,因為許多 Wnt 信號傳導蛋白在癲癇發作后也急劇升高。
有關 β-連環蛋白在癲癇發作所起作用的前期研究發現,電驚厥性癲癇發作上調了大鼠海馬新生神經元中 β-連環蛋白和 Wnt 2 配體基因表達[19]。升高的 β-連環蛋白定位于齒狀回的亞粒區(SGZ),齒狀回是成年哺乳動物腦中能夠在整個壽命期間產生新神經元的兩個區域之一。Pirone 等[20]研究發現 APC 條件性敲除小鼠(APC cko)神經元內 β-連環蛋白表達水平增加,伴有明顯的多種類型的痙攣發作。另一項研究發現,局灶性皮質缺血后 Wnt/β-連環蛋白信號在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中升高。與野生型(WT)小鼠相比,Catnb 小鼠對戊四氮(PTZ)誘導的癲癇發作易感性增加,包括癲癇/死亡的潛伏期縮短和癲癇發作次數增加,且表現為皮質發育異常[21]。總之,這些研究強調了癲癇動物模型中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在控制癲癇易感性、神經發生和潛在癲癇發生中的重要性。
基因表達研究還強調了嚙齒動物模型中實驗誘導癲癇發作后 Wnt 信號通路的作用。一項基因表達譜分析研究發現,在出生后第 10 天缺氧誘導癲癇發作,12 h 后 Wnt/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組分大量表達,包括 β-連環蛋白(CTNNB1)基因、共受體 LRP6、Fz 配體(WNT2、WNT5A、WNT10 A)和 β-連環蛋白破壞復合物組分(GSK3β、AXIN2、APC)[22]。另一項涉及癲癇相關 microRNA(miRNA)表達和信號通路調控的研究發現,在顳葉癲癇模型(TLE)中,癲癇持續狀態(Status epilepticus,SE)后大鼠 Wnt 信號通路靶基因(Wnt3、Fzd5、Dvl2、Dkk-2)miRNA 顯著上調或下調[23],表明沉默或激活 Wnt 通路靶基因的特定 miRNA 具有治療潛力。
2.2 癲癇患者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靶向治療效果
目前,抗癲癇藥物(AEDs)的機制主要是降低神經元興奮性和調節離子通道功能[提高 γ-氨基丁酸(GABA)能神經傳遞、降低谷氨酸能神經傳遞、抑制電壓門控離子通道和改變細胞內信號轉導通路等][1],以預防或減少大腦的癲癇活動,從而阻止或減少癲癇發作。雖然有多種類型的 AEDs 可用,但約 1/3 的癲癇患者仍對治療產生抵抗,約 30% 的患者存在多藥耐藥(通過至少 3 種合適的 AEDs 足量、足療程治療后癲癇癥狀仍然存在)。針對耐藥癲癇,尋找替代的更有效的治療方法至關重要。
新型抗癲癇治療方案的研究不應該局限于對神經元興奮性和控制失衡的直接作用,而應關注癲癇發作后被破壞的細胞機制。有大量證據表明,癲癇發作后 Wnt/β-連環蛋白活性發生改變且該途徑在調節神經元死亡和神經發生中起作用。因此,該途徑的新靶點可能在未來的癲癇治療中具有重要的治療潛力[24]。干預 Wnt/β-連環蛋白途徑會影響癲癇發作時腦內的潛在分子機制,因此,與現有的 AEDs 相比,能從根本上遏制癲癇電活動的發生及病程的進展。
典型的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可以受到多種不同機制的影響,包括已經獲批準和廣泛應用的藥物,以及許多靶向信號傳導通路的小分子組分。GSK3β 是一種較好的研究靶點,對恢復 Wnt/β-連環蛋白穩態具有良好效果。GSK3β 的抑制阻止了 β-連環蛋白的磷酸化和破壞,從而使得 β-連環蛋白積累并易位進入細胞核以激活下游基因。Busceti 等[25]發現,在臨床實踐中廣泛使用的 GSK3β 抑制劑氯化鋰能在大鼠紅藻氨酸(KA)致癲癇發作后 7 d 保護其免于癲癇發作誘導的海馬神經元損傷。除氯化鋰外,還有許多其他化合物和內源性化學物質可以抑制 GSK3β 活性,從而恢復 Wnt 信號通路的穩定,包括 kenpaullone、SB-216763、L807mts、LY2090314、NPO3112(tideglusib),雌激素和廣泛使用的 AEDs 丙戊酸鈉[11, 26]。研究表明,這些化合物可在各種環境下有效促進神經發生,然而,在體內癲癇模型中直接檢測 GSK3β 抑制對癲癇發作效果的研究仍有限。
調節 Wnt 信號通路活性的另一種潛在機制是 Wnt 途徑的靶向內源性拮抗劑。例如,Dkk-1 通過與共受體 LRP5/6 相互作用選擇性地拮抗 Wnt 信號傳導,從而阻止受體與 Wnt 配體結合。Dkk-1 參與大腦神經元的生理性調節,而其在癲癇灶中的過表達影響正常 Wnt 途徑的穩定。在該 TLE 大鼠模型中神經元死亡前的急性期,KA 誘導癲癇發作后,Dkk-1 表達增加[27]。此外,用反義寡核苷酸敲低 Dkk-1 能夠對抗大鼠癲癇發作誘導的神經元死亡。TLE 患者的海馬組織也顯示出 Dkk-1 高表達,Dkk-1 拮抗劑可能是降低 TLE 相關神經元損傷程度的有益靶標。而雌二醇(E2)在維持 Dkk1 和 Wnt/β 連環蛋白信號傳導的平衡中起到重要作用[27]。除了 Dkk 蛋白外,還有許多其他內源性配體可拮抗 Wnt/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這些可能是恢復 Wnt 信號通路的潛在靶點,包括 Wnt 抑制因子-1(WIF-1)、分泌性卷曲蛋白相關蛋白(sFRPs)、Shisa 蛋白和 Wise/SOST 家族中的蛋白質[28]。
除內源性配體外,還存在多種 Wnt 信號通路的小分子抑制劑,在癲癇發作急性期(Wnt 通路活性通常升高)應用可帶來益處。然而,這些尚未在癲癇模型中進行研究。Axin 是 β-連環蛋白破壞復合物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作為潛在靶點。一些分子,如 XAV939 和 IWR,可抑制端錨聚合酶,這是一種調節 β-連環蛋白破壞復合物中 Axin 穩定性聚合酶。因此,這些化合物(XAV939、IWR)激活并增加 Axin 水平,導致 β-連環蛋白降解增加和 Wnt 靶基因轉錄減少[17]。其他化合物如 IWP2、C59 和 LGK974,具有抑制 Porcupine 的作用。Porcupine 是負責催化 Wnt 配體蛋白酰化的酶。這些分子可能降低 Wnt 配體表達并抑制整個 Wnt 通路的活性[29]。
當抑制癲癇發作后的 Wnt 活性時,Wnt 介導的其他作用也會受到影響。信號傳導對于許多正常細胞過程(如突觸傳遞和可塑性)的調節也非常關鍵。評估癲癇發作后 Wnt 信號傳導降低對認知造成的影響也非常重要,因為抑制 Wnt 活性可損害長期強化并可能對學習和記憶產生不利影響。Wnt 抑制具有神經保護和潛在認知副作用雙重效應,應繼續研究癲癇發作后抑制途徑的最佳時間和方法。
3 展望
綜上,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與癲癇的多個方面密切相關,包括癲癇發作誘導的神經發生、癲癇發作易感性,以及慢性癲癇的潛在發展。然而,研究結果相對有限,并且該通路的組分如何直接或間接介導癲癇發生的機制需要進一步研究。一些研究利用嚙齒動物癲癇模型,檢測癲癇發作后急性和慢性期神經發生。多數研究發現,Wnt 蛋白水平與這些時間段沒有相關性。因此,在癲癇發作和進展的不同階段,該通路影響神經發生的動態變化仍需更多的研究。為了進一步明確在何時、如何干涉該途徑從而使其作為癲癇的治療的靶標最有益,繼續相關研究仍很重要。當在癲癇發作后干預 Wnt 信號傳導時,必須檢測和觀察該干預對 Wnt 介導下游通路的影響。
綜上,目前癲癇治療以藥物為主,而 AEDs 的作用機制一般是對離子通道和神經遞質的影響,很少涉及癲癇發作的分子機制。耐藥性癲癇的存在使得具有分子靶向治療的新型 AEDs 研究成為熱點,這些治療可以使患者潛在性地減少藥物抵抗的可能性,并且有助于減輕癲癇發作相關的認知缺陷。癲癇發作后失調的 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和其他細胞信號級聯反應,將有望成為未來抗癲癇治療的選擇靶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