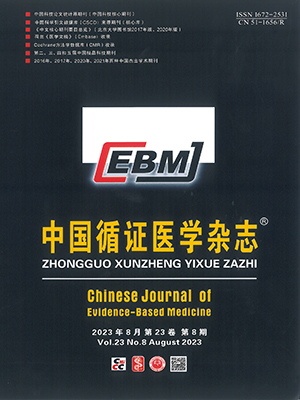引用本文: 溫秋月, 盧東民, 姜寶榮, 姚金蘭, 沈旭慧, 沈麗娟, 沈建通, 江琪, 張奕. 我國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8, 18(6): 617-623. doi: 10.7507/1672-2531.201711121 復制
健康城市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為應對快速城市化進程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提出的一項全球性戰略計劃[1, 2],也是推進“健康中國”目標的重要抓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健康城市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是確定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其不僅可用來監督健康城市的建設和評估建設過程,也是體現建設目標和建設原則的主要內容之一[3]。2016 年,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印發的《關于開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的指導意見》[4]要求到 2017 年建立健全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鎮建設管理機制,形成一套科學、有效、可行的健康城市指標和評價體系。目前,我國各城市已陸續開展健康城市的建設與探索,也出臺了各自的指標體系,但具體指標的選用、設置、詮釋因缺乏規范而差異較大,科學性、合理性和側重點不一。本研究旨在全面收集與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相關的文獻,進行定性分析并與 WHO 標準比較,為國家健康城市指標和評價體系制定提供基線數據,同時也為其他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選用提供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標準
納入明確提及健康城市及其指標體系的研究。文獻類型包括:綜述、原始研究和政策文件(即政府及相關部門發布的通知、意見或決定)。如同一個城市發布了多個不同時段的指標體系則納入最新指標體系。
1.2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的研究;② 僅提到健康城市指標但無具體指標內容或僅有部分指標的文獻。
1.3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手工檢索 WHO 網站、我國各省市政府網、國家及各省市衛生計生委網站及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網站,檢索時限從建庫截至 2017 年 3 月。中文檢索詞包括:健康城市、城市健康、指標;英文檢索詞包括:urban health、healthy cities、healthy city、indicator、indicators、index 等。以 CNKI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4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 2 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建立原則、方法、具體指標。
1.5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參考中國循證醫學中心對非運非藥類研究證據的分級方法進行評價[5]。
1.6 統計分析
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對納入研究進行分類歸納和描述。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文獻數據庫獲得 560 篇相關文獻,在網站獲得 49 篇相關政策文件,經過閱讀標題、摘要和全文,最終納入 26 篇文章[6-31],包括 4 篇研究[17, 24, 28, 31]和 22 篇政策文件[6-16, 18-23, 25-27, 29, 30],涉及 24 個城市。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CNKI(
2.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2 篇政府及相關機構報告評為 B 級證據,4 篇有確切研究方法的文獻評為 C 級證據。
2.3 健康城市指標體系
我國 24 個城市的健康城市指標匯總結果見表 1。
2.3.1 健康維度
24 個城市均設置了健康維度,包含 82 個指標。其中人均期望壽命、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 3 個指標使用頻率最高,均超過 20 次。其次使用頻率≥5 次的指標依次為: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口比例、人群吸煙率、出生缺陷發生率、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國民體質監測合格率和居民健康行為形成率 6 個指標。其余指標選用頻率均<4 次,57 個指標僅被選用 1 次。此外,13 個指標涉及知識知曉率,10 個指標涉及死亡率,6 個指標涉及慢性病管理,6 個指標涉及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5 個指標涉及傳染病發病率,3 個指標涉及兒童預防接種,3 個指標涉及肥胖率。
2.3.2 健康服務維度
23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服務維度,包含 113 個指標。選用頻率均≥5 次的指標依次為:每千(每萬)常住人口執業(助理)醫師數、每千常住人口實有(醫院衛生院)床位數、精神疾病患者(有效)管理(治療)率、每千名老年人口社會養老床位數和千人(萬人)注冊護士數 5 個指標;74 個指標選用頻率為 1 次。此外,12 個指標涉及慢性病管理,11 個指標涉及傳染病管理,8 個指標涉及健康管理率,8 個指標涉及公共設施建設,6 個指標涉及基本醫療服務覆蓋率,5 個指標涉及基本醫療服務達標率,5 個指標涉及兒童預防接種,5 個指標涉及全民健身,3 個指標涉及公共衛生服務經費,3 個指標涉及職業病監測。
2.3.3 健康環境維度
21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環境維度,包含 121 個指標。選用頻率≥5 次的指標依次為: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綠化覆蓋率、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水質達標率、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森林覆蓋率、區域環境噪音平均值、體育設施面積、農村無害化廁所普及率和生活飲用水水質合格率 10 個指標;80 個指標選用頻率為 1 次。此外,13 個指標涉及城市建設榮譽稱號,13 個指標涉及飲用水達標率,9 個指標涉及大氣污染控制,8 個指標涉及食品安全管理,6 個指標涉及公廁管理,5 個指標涉及生活垃圾處理,5 個指標涉及公共交通出行,4 個指標涉及污水處理,4 個指標涉及綠化覆蓋率,4 個指標涉及污染物排放,3 個指標涉及噪聲污染控制。
2.3.4 健康社會維度
18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社會維度,包含 113 個指標。選用頻率≥5 次的指標依次為:城鎮失業率、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和無煙公共/工作場所 6 個指標;76 個指標選用頻率為 1 次。此外,17 個指標涉及食品安全管理,10 個指標涉及困難人群社會保障,7 個指標涉及禁煙,7 個指標涉及醫療保險,7 個指標涉及經濟水平,6 個指標涉及工傷、失業、生育保險,4 個指標涉及養老保險。
2.3.5 民意指標維度
16 個城市設置了民意指標維度,包含 20 個指標。選用頻率≥5 次的指標依次為:市民對衛生服務滿意度、市民對交通狀況滿意度、市民對食品安全滿意度、市民對社會治安滿意度、市民對社會保障滿意度和市民對環境質量滿意度 6 個指標。8 個指標選用頻率為 1 次,其中,4 個指標涉及市民對環境衛生的滿意度。
2.3.6 政策指標維度
8 個城市設置了政府指標維度,包含 20 個指標。前 4 位的指標依次為組織健全、政府重視、部門合作、考核獎勵,使用頻率均≥4 次,其余指標選用≤2 次。在 13 個選用頻率為 1 次的指標中,3 個指標涉及組織健全,3 個指標涉及考核獎勵,2 個指標涉及健康城市經費支持,2 個指標涉及制定健康城市工作計劃,3 個指標為其他。
2.3.7 健康促進維度
7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促進維度,包含 42 個指標。涉及控煙、健康膳食、全民健身、細胞工程等方面。前 8 位的指標依次為健康社區、健康醫院、健康村、健康家庭、健康學校、健康機關、健康企業、健康步道,使用頻率均≥3 次。在 30 個選用頻率為 1 次的指標中,18 個指標涉及細胞工程,3 個指標涉及全民健身工程,3 個指標涉及健康促進榮譽稱號,3 個指標涉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榮譽稱號,2 個指標涉及禁煙,1 個指標為其他。
2.3.8 健康文化維度
僅 7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文化維度,包含 17 個指標。使用頻率前 3 位的指標分別是居民健康素養水平、居民健康知識知曉率、每萬人擁有注冊志愿者人數,使用頻率均≥2 次。在 14 個選用頻率為 1 次的指標中,7 個指標涉及健康知識的傳播,3 個指標涉及知識知曉率,4 個指標為其他。
2.3.9 其他維度
共 4 個城市設置了其他維度,包含 18 個指標。僅健康城市特色活動和榮譽稱號兩個指標使用頻率為 2 次,其余 16 個指標使用頻率為 1 次。健康食品維度僅蘇州設置,含 6 個指標。健康產業維度僅杭州設置,含 3 個指標。健康行動維度僅舟山設置,含 56 個指標,8 個指標涉及基本衛生服務,4 個指標涉及醫療服務經費保障,2 個指標涉及就業率,2 個指標涉及知識知曉率。健康行為維度,僅青島設置,共 8 個指標,其中 4 個指標涉及居民滿意度,2 個指標涉及健康城市政策。
此外,2 個城市有其獨特的健康城市指標。如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設的 5 項市民行動包括“清潔環境”、“科學健身”、“控制煙害”、“食品安全”和“正確就醫”,是上海市建設健康城市的第5輪行動,包括 32 個指標,其中 6 個指標涉及知曉率,4 個涉及指標健康行為形成率[32]。瀘州市健康城市指標 由健康環境營造工程、食品安全保障工程、健康細胞建設工程、健康文化推進工程、全民預防保健工程、全民健身工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完善工程和創新發展工程 8 個專項工程和群眾滿意度指標組成[33]。
3 討論
3.1 我國健康城市指標分析
健康城市的終極目標是提升城市中生活及工作人群的身體、精神、社會和環境福祉。健康指標本質上是對健康和福祉的數值度量[30]。WHO 公布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涵蓋健康、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和社會經濟情況4方面[34]。本研究發現,盡管由于文化和國情的不同,在指標具體的表達上存在一定差異,但我國健康城市指標總體內容結構與 WHO 較一致,且增加了民意指標、政策指標等特色內容。
與國際慣例不同的是,我國將醫療保險放在健康社會維度,而 WHO 將其放在健康服務維度下。我國健康城市指標專門設置政策指標維度,強調健康城市建設過程中政府角色和多部門協作,這與 2016 年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上達成的《上海宣言》[35]對政府和多部門的要求一致。但我國不同城市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普遍存在指標的劃分與定義不符,存在不同城市將同一類指標劃分至不同維度的現象,還有如健康服務維度中有體育設施用地面積、食品安全、自行車擁有量等 20 個與維度定義不符的指標,暴露出健康城市對維度和指標的內涵界定不清的問題,可能需要統一和規范。
3.2 我國健康城市指標的特點
① 城市與村鎮并重。我國健康城市指標中,46 個指標涉及農村,涵蓋社會保險、健康檔案、基礎設施建設等,其中 21 個兼顧城鄉,4 個兼顧流動人口。② 多樣性與特色性并存。26 個健康城市指標涵蓋了健康水平、環境問題、醫療衛生服務、社會保障、居民滿意度等不同方面。由于我國地區差異顯著,健康城市進度不一,故指標體系反應了當地實際和特色。如杭州依托電子產業近年來的高速發展,率先使用智慧醫療覆蓋率的指標,側重于健康產業的建立[7];上海是我國最早開展健康城市建設的城市之一,突破了健康影響因素的框架,指標與行動相結合,針對性強,側重于全民參與[32]。③ 體現民意,全民參與。有 16 個城市設置了民意指標維度,而青島[28]、瀘州[33]、上海[32]均設置了滿意度指標,可見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重視居民的感受和意見,強調調動市民參與健康城市的行動,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④ 政策保障。我國健康城市普遍設置煙草管理、食品安全、全民健身、慢性病非傳染病管理等涉及我國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指標。同時,隨著《食品安全法》、《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等政策法規陸續出臺,在建設健康城市的道路上始終有法律法規的保障。
3.3 健康城市指標設置的建議
3.3.1 增設心理精神健康指標
中國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36],“城市病”日益凸顯,研究指出“城市病”在人與人之間的微觀層面,主要表現為個體心理精神疾病,存在人與人關系的異化現象[37]。2015 年相關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約 1.73 億人患有精神疾病[39]。心理與精神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應是健康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39],我國健康城市普遍缺少測量居民心理精神健康的指標,僅局限于重性精神患者管理的指標。而僅使用身體健康的指標不能準確和全面地反映城市人群的健康水平。故我們建議未來引入心理精神專業,針對不同地區的特點選取指標,對人群心理健康進行測量和評價,增設心理衛生指標(如心理健康水平、抑郁癥發病率等)[40, 41]。
3.3.2 增設兒童、孕產婦、老年等重點人群相關指標
全國愛衛辦在建設健康城市健康村鎮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強化婦幼健康工作[4]。兒童及孕產婦健康是評價一個國家和地區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42, 43],2016 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為 19.9/10 萬,嬰兒死亡率、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分別為 7.5‰和 10.2‰,二孩比例和高齡高危孕產婦比例明顯增高[44]。而目前我國健康城市針對婦幼健康的指標普遍僅以死亡率和預防接種率為主,鮮有婦幼身心健康相關指標。同時,我國老齡化程度快速上升,高齡老人口持續增長,截至 2016 年底 65 歲以上人口已達到 10.8%[45-47],而我國健康城市針對老年人群的指標僅限于養老床位,缺乏老年健康相關指標。建議增設兒童、孕產婦、老年等重點人群相關指標(如弱勢兒童受照顧率、獨居老人受照顧率、高齡高危孕產婦比例等)[44, 48]。
3.3.3 科學設置指標數量
健康城市評價指標的最佳數量由許多因素決定,包括收集時間、可獲得的資源和社區的特定需求[7]。如指標數量過多,則指標的收集和后續分析存在較大挑戰;指標過少,則不能全面地反映城市健康問題。WHO 最初建立了 12 類 338 項可量化健康城市評估指標,但在實踐過程中逐一刪減、修訂至 32 項[31, 49, 50]。我國的蘇州[8]、重慶[17]、義烏[21]、舟山[23]4 個城市的指標數量均超過 100 個,蘇州曾明確指出為了便于數據的獲得,在指標體系中較多選用了各部門工作指標來反映健康城市的成效,而缺乏真正反映健康城市建設效果的指標[8]。健康城市被定義為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51],其建設分為不同的階段,由連續的周期組成,識別城市在每個建設周期的特定需求和急需解決的健康問題,綜合考量可獲得的資源是確認健康城市指標最佳數量的依據。
本研究局限性:① 由于部分城市的政府或相關部門未公布已經確立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或未獲得相關文獻,以上原因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② 本文僅限于健康城市指標的比較,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結構和維度設置評價見另文。
綜上所述,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內容與國際基本一致,同時具有多樣性、特色性、政策性、全民性等特點,但也存在指標數量過多、指標詮釋不一、類別劃分不當、缺少心理健康、兒童、孕產婦、老人健康指標等問題,急需制定健康城市指標設置的原則、方法、流程和規范。
健康城市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為應對快速城市化進程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提出的一項全球性戰略計劃[1, 2],也是推進“健康中國”目標的重要抓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健康城市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是確定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其不僅可用來監督健康城市的建設和評估建設過程,也是體現建設目標和建設原則的主要內容之一[3]。2016 年,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印發的《關于開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的指導意見》[4]要求到 2017 年建立健全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鎮建設管理機制,形成一套科學、有效、可行的健康城市指標和評價體系。目前,我國各城市已陸續開展健康城市的建設與探索,也出臺了各自的指標體系,但具體指標的選用、設置、詮釋因缺乏規范而差異較大,科學性、合理性和側重點不一。本研究旨在全面收集與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相關的文獻,進行定性分析并與 WHO 標準比較,為國家健康城市指標和評價體系制定提供基線數據,同時也為其他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選用提供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標準
納入明確提及健康城市及其指標體系的研究。文獻類型包括:綜述、原始研究和政策文件(即政府及相關部門發布的通知、意見或決定)。如同一個城市發布了多個不同時段的指標體系則納入最新指標體系。
1.2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的研究;② 僅提到健康城市指標但無具體指標內容或僅有部分指標的文獻。
1.3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手工檢索 WHO 網站、我國各省市政府網、國家及各省市衛生計生委網站及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網站,檢索時限從建庫截至 2017 年 3 月。中文檢索詞包括:健康城市、城市健康、指標;英文檢索詞包括:urban health、healthy cities、healthy city、indicator、indicators、index 等。以 CNKI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4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 2 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建立原則、方法、具體指標。
1.5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參考中國循證醫學中心對非運非藥類研究證據的分級方法進行評價[5]。
1.6 統計分析
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對納入研究進行分類歸納和描述。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文獻數據庫獲得 560 篇相關文獻,在網站獲得 49 篇相關政策文件,經過閱讀標題、摘要和全文,最終納入 26 篇文章[6-31],包括 4 篇研究[17, 24, 28, 31]和 22 篇政策文件[6-16, 18-23, 25-27, 29, 30],涉及 24 個城市。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CNKI(
2.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2 篇政府及相關機構報告評為 B 級證據,4 篇有確切研究方法的文獻評為 C 級證據。
2.3 健康城市指標體系
我國 24 個城市的健康城市指標匯總結果見表 1。
2.3.1 健康維度
24 個城市均設置了健康維度,包含 82 個指標。其中人均期望壽命、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 3 個指標使用頻率最高,均超過 20 次。其次使用頻率≥5 次的指標依次為: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口比例、人群吸煙率、出生缺陷發生率、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國民體質監測合格率和居民健康行為形成率 6 個指標。其余指標選用頻率均<4 次,57 個指標僅被選用 1 次。此外,13 個指標涉及知識知曉率,10 個指標涉及死亡率,6 個指標涉及慢性病管理,6 個指標涉及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5 個指標涉及傳染病發病率,3 個指標涉及兒童預防接種,3 個指標涉及肥胖率。
2.3.2 健康服務維度
23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服務維度,包含 113 個指標。選用頻率均≥5 次的指標依次為:每千(每萬)常住人口執業(助理)醫師數、每千常住人口實有(醫院衛生院)床位數、精神疾病患者(有效)管理(治療)率、每千名老年人口社會養老床位數和千人(萬人)注冊護士數 5 個指標;74 個指標選用頻率為 1 次。此外,12 個指標涉及慢性病管理,11 個指標涉及傳染病管理,8 個指標涉及健康管理率,8 個指標涉及公共設施建設,6 個指標涉及基本醫療服務覆蓋率,5 個指標涉及基本醫療服務達標率,5 個指標涉及兒童預防接種,5 個指標涉及全民健身,3 個指標涉及公共衛生服務經費,3 個指標涉及職業病監測。
2.3.3 健康環境維度
21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環境維度,包含 121 個指標。選用頻率≥5 次的指標依次為: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綠化覆蓋率、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水質達標率、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森林覆蓋率、區域環境噪音平均值、體育設施面積、農村無害化廁所普及率和生活飲用水水質合格率 10 個指標;80 個指標選用頻率為 1 次。此外,13 個指標涉及城市建設榮譽稱號,13 個指標涉及飲用水達標率,9 個指標涉及大氣污染控制,8 個指標涉及食品安全管理,6 個指標涉及公廁管理,5 個指標涉及生活垃圾處理,5 個指標涉及公共交通出行,4 個指標涉及污水處理,4 個指標涉及綠化覆蓋率,4 個指標涉及污染物排放,3 個指標涉及噪聲污染控制。
2.3.4 健康社會維度
18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社會維度,包含 113 個指標。選用頻率≥5 次的指標依次為:城鎮失業率、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和無煙公共/工作場所 6 個指標;76 個指標選用頻率為 1 次。此外,17 個指標涉及食品安全管理,10 個指標涉及困難人群社會保障,7 個指標涉及禁煙,7 個指標涉及醫療保險,7 個指標涉及經濟水平,6 個指標涉及工傷、失業、生育保險,4 個指標涉及養老保險。
2.3.5 民意指標維度
16 個城市設置了民意指標維度,包含 20 個指標。選用頻率≥5 次的指標依次為:市民對衛生服務滿意度、市民對交通狀況滿意度、市民對食品安全滿意度、市民對社會治安滿意度、市民對社會保障滿意度和市民對環境質量滿意度 6 個指標。8 個指標選用頻率為 1 次,其中,4 個指標涉及市民對環境衛生的滿意度。
2.3.6 政策指標維度
8 個城市設置了政府指標維度,包含 20 個指標。前 4 位的指標依次為組織健全、政府重視、部門合作、考核獎勵,使用頻率均≥4 次,其余指標選用≤2 次。在 13 個選用頻率為 1 次的指標中,3 個指標涉及組織健全,3 個指標涉及考核獎勵,2 個指標涉及健康城市經費支持,2 個指標涉及制定健康城市工作計劃,3 個指標為其他。
2.3.7 健康促進維度
7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促進維度,包含 42 個指標。涉及控煙、健康膳食、全民健身、細胞工程等方面。前 8 位的指標依次為健康社區、健康醫院、健康村、健康家庭、健康學校、健康機關、健康企業、健康步道,使用頻率均≥3 次。在 30 個選用頻率為 1 次的指標中,18 個指標涉及細胞工程,3 個指標涉及全民健身工程,3 個指標涉及健康促進榮譽稱號,3 個指標涉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榮譽稱號,2 個指標涉及禁煙,1 個指標為其他。
2.3.8 健康文化維度
僅 7 個城市設置了健康文化維度,包含 17 個指標。使用頻率前 3 位的指標分別是居民健康素養水平、居民健康知識知曉率、每萬人擁有注冊志愿者人數,使用頻率均≥2 次。在 14 個選用頻率為 1 次的指標中,7 個指標涉及健康知識的傳播,3 個指標涉及知識知曉率,4 個指標為其他。
2.3.9 其他維度
共 4 個城市設置了其他維度,包含 18 個指標。僅健康城市特色活動和榮譽稱號兩個指標使用頻率為 2 次,其余 16 個指標使用頻率為 1 次。健康食品維度僅蘇州設置,含 6 個指標。健康產業維度僅杭州設置,含 3 個指標。健康行動維度僅舟山設置,含 56 個指標,8 個指標涉及基本衛生服務,4 個指標涉及醫療服務經費保障,2 個指標涉及就業率,2 個指標涉及知識知曉率。健康行為維度,僅青島設置,共 8 個指標,其中 4 個指標涉及居民滿意度,2 個指標涉及健康城市政策。
此外,2 個城市有其獨特的健康城市指標。如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設的 5 項市民行動包括“清潔環境”、“科學健身”、“控制煙害”、“食品安全”和“正確就醫”,是上海市建設健康城市的第5輪行動,包括 32 個指標,其中 6 個指標涉及知曉率,4 個涉及指標健康行為形成率[32]。瀘州市健康城市指標 由健康環境營造工程、食品安全保障工程、健康細胞建設工程、健康文化推進工程、全民預防保健工程、全民健身工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完善工程和創新發展工程 8 個專項工程和群眾滿意度指標組成[33]。
3 討論
3.1 我國健康城市指標分析
健康城市的終極目標是提升城市中生活及工作人群的身體、精神、社會和環境福祉。健康指標本質上是對健康和福祉的數值度量[30]。WHO 公布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涵蓋健康、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和社會經濟情況4方面[34]。本研究發現,盡管由于文化和國情的不同,在指標具體的表達上存在一定差異,但我國健康城市指標總體內容結構與 WHO 較一致,且增加了民意指標、政策指標等特色內容。
與國際慣例不同的是,我國將醫療保險放在健康社會維度,而 WHO 將其放在健康服務維度下。我國健康城市指標專門設置政策指標維度,強調健康城市建設過程中政府角色和多部門協作,這與 2016 年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上達成的《上海宣言》[35]對政府和多部門的要求一致。但我國不同城市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普遍存在指標的劃分與定義不符,存在不同城市將同一類指標劃分至不同維度的現象,還有如健康服務維度中有體育設施用地面積、食品安全、自行車擁有量等 20 個與維度定義不符的指標,暴露出健康城市對維度和指標的內涵界定不清的問題,可能需要統一和規范。
3.2 我國健康城市指標的特點
① 城市與村鎮并重。我國健康城市指標中,46 個指標涉及農村,涵蓋社會保險、健康檔案、基礎設施建設等,其中 21 個兼顧城鄉,4 個兼顧流動人口。② 多樣性與特色性并存。26 個健康城市指標涵蓋了健康水平、環境問題、醫療衛生服務、社會保障、居民滿意度等不同方面。由于我國地區差異顯著,健康城市進度不一,故指標體系反應了當地實際和特色。如杭州依托電子產業近年來的高速發展,率先使用智慧醫療覆蓋率的指標,側重于健康產業的建立[7];上海是我國最早開展健康城市建設的城市之一,突破了健康影響因素的框架,指標與行動相結合,針對性強,側重于全民參與[32]。③ 體現民意,全民參與。有 16 個城市設置了民意指標維度,而青島[28]、瀘州[33]、上海[32]均設置了滿意度指標,可見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重視居民的感受和意見,強調調動市民參與健康城市的行動,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④ 政策保障。我國健康城市普遍設置煙草管理、食品安全、全民健身、慢性病非傳染病管理等涉及我國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指標。同時,隨著《食品安全法》、《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等政策法規陸續出臺,在建設健康城市的道路上始終有法律法規的保障。
3.3 健康城市指標設置的建議
3.3.1 增設心理精神健康指標
中國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36],“城市病”日益凸顯,研究指出“城市病”在人與人之間的微觀層面,主要表現為個體心理精神疾病,存在人與人關系的異化現象[37]。2015 年相關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約 1.73 億人患有精神疾病[39]。心理與精神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應是健康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39],我國健康城市普遍缺少測量居民心理精神健康的指標,僅局限于重性精神患者管理的指標。而僅使用身體健康的指標不能準確和全面地反映城市人群的健康水平。故我們建議未來引入心理精神專業,針對不同地區的特點選取指標,對人群心理健康進行測量和評價,增設心理衛生指標(如心理健康水平、抑郁癥發病率等)[40, 41]。
3.3.2 增設兒童、孕產婦、老年等重點人群相關指標
全國愛衛辦在建設健康城市健康村鎮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強化婦幼健康工作[4]。兒童及孕產婦健康是評價一個國家和地區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42, 43],2016 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為 19.9/10 萬,嬰兒死亡率、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分別為 7.5‰和 10.2‰,二孩比例和高齡高危孕產婦比例明顯增高[44]。而目前我國健康城市針對婦幼健康的指標普遍僅以死亡率和預防接種率為主,鮮有婦幼身心健康相關指標。同時,我國老齡化程度快速上升,高齡老人口持續增長,截至 2016 年底 65 歲以上人口已達到 10.8%[45-47],而我國健康城市針對老年人群的指標僅限于養老床位,缺乏老年健康相關指標。建議增設兒童、孕產婦、老年等重點人群相關指標(如弱勢兒童受照顧率、獨居老人受照顧率、高齡高危孕產婦比例等)[44, 48]。
3.3.3 科學設置指標數量
健康城市評價指標的最佳數量由許多因素決定,包括收集時間、可獲得的資源和社區的特定需求[7]。如指標數量過多,則指標的收集和后續分析存在較大挑戰;指標過少,則不能全面地反映城市健康問題。WHO 最初建立了 12 類 338 項可量化健康城市評估指標,但在實踐過程中逐一刪減、修訂至 32 項[31, 49, 50]。我國的蘇州[8]、重慶[17]、義烏[21]、舟山[23]4 個城市的指標數量均超過 100 個,蘇州曾明確指出為了便于數據的獲得,在指標體系中較多選用了各部門工作指標來反映健康城市的成效,而缺乏真正反映健康城市建設效果的指標[8]。健康城市被定義為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51],其建設分為不同的階段,由連續的周期組成,識別城市在每個建設周期的特定需求和急需解決的健康問題,綜合考量可獲得的資源是確認健康城市指標最佳數量的依據。
本研究局限性:① 由于部分城市的政府或相關部門未公布已經確立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或未獲得相關文獻,以上原因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② 本文僅限于健康城市指標的比較,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結構和維度設置評價見另文。
綜上所述,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內容與國際基本一致,同時具有多樣性、特色性、政策性、全民性等特點,但也存在指標數量過多、指標詮釋不一、類別劃分不當、缺少心理健康、兒童、孕產婦、老人健康指標等問題,急需制定健康城市指標設置的原則、方法、流程和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