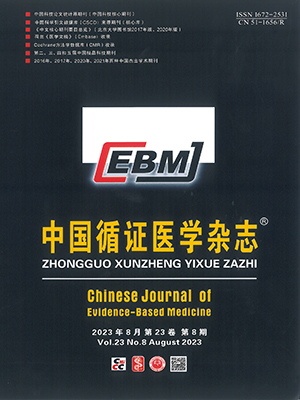引用本文: 王建華, 肖蕾, 張哲, 何麗云, 閆世艷, 王鑫, 楊關林. 心腦合病危險因素的橫斷面調查.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4, 14(4): 408-413. doi: 10.7507/1672-2531.20140071 復制
冠心病心絞痛和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同屬于動脈粥樣硬化性疾病[1, 2]。由于致病因素、病理基礎等高度一致,臨床上出現越來越多的同患兩病的患者。上述兩病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給患者帶來了極大的痛苦,給家庭及社會造成了沉重的負擔。針對這一現狀,楊關林教授基于多年臨床實踐及科學研究首次提出“心腦合病”的概念[3, 4]來研究如何預防和治療心腦合病,以降低死亡率和致殘率。目前國內外關于心腦合病的研究報道較少,有關心腦合病危險因素的流行病學分析性研究亦少見,本研究旨在通過與單一心病或腦病危險因素的對比,揭示心腦合病的危險因素,為預防心腦合病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橫斷面調查研究方法。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從我國11家三甲醫院納入符合標準的冠心病心絞痛患者。這11家醫院包括: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遼寧省中醫藥研究院)、遼寧省血栓病中西醫結合醫療中心、大連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撫順市中醫院、丹東市中醫院、營口市中醫院、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盛京醫院)、中國中醫研究院附屬西苑醫院、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沈陽軍區總醫院。
1.2 調查對象的篩選
1.2.1 心腦合病
1.2.1.1 納入標準
①符合冠心病心絞痛,同時符合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2~8周)診斷標準;②年齡在35~85歲;③簽署知情同意書。
1.2.1.2 排除標準
①風濕性心臟病、甲亢性心臟病、心肌炎、心肌病、高心病等非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②心肌梗死,無癥狀性心肌缺血、缺血性心肌病等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③腦栓塞、腦出血、短暫性腦缺血發作、腔隙性腦梗死;④除動脈粥樣硬化以外其他原因所致的腦梗死,如動脈炎、腦腫瘤、腦外傷、腦寄生蟲、代謝障礙、真性紅細胞增多癥、血栓性栓塞、顱內血管畸形、腦淀粉樣變性等。
1.2.1.3 剔除標準
①不符合診斷、納入標準而被誤納入者;②觀察中無任何可利用數據者。
1.2.1.4 診斷標準
不穩定性心絞痛的診斷按中華醫學會2007年公布的《不穩定性心絞痛和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診斷與治療指南》 [5];穩定性心絞痛的診斷按《中國慢性穩定性心絞痛診斷與治療指南》 [6](2007年);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的診斷按1995年中華醫學會制定的《各類腦血管病診斷要點》 [7],并參照《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 [8](2005年)。
1.2.2 冠心病心絞痛
診斷標準、剔除標準、納入標準、排除標準同心腦合病中涉及的冠心病心絞痛的各項標準。
1.2.3 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
診斷標準、剔除標準、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同心腦合病中涉及的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的各項標準。
1.3 調查內容和方法
由經過培訓的臨床研究人員使用統一的流行病學調查表對調查對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包括患者的一般情況(姓名、職業、出生地等)和危險因素(體重、血壓、血脂、血糖等)等。
1.4 危險因素判定標準
對每例患者均進行詳細的病史詢問和仔細的體格檢查、理化檢驗,危險因素按下列標準確定:①高血壓:既往有高血壓史或新診斷的高血壓,采用美國JNCⅦ指南標準,連續2次在靜息狀態下收縮壓(SBP)≥140 mmHg和/或舒張壓(DBP)≥90 mmHg;②糖尿病:既往已確診的糖尿病或新診斷的糖尿病,采用美國糖尿病協會標準診斷,空腹血糖≥7.0 mmol/L和/或餐后2小時血糖≥11.1 mmol/ L;③高脂血癥:既往有明顯的高脂血癥或入院后經生化檢查發現血脂增高,血清總膽固醇(TC)≥5.20 mmol/L或甘油三酯(TG)≥1.70 mmol/L或LDLC≥2.60 mmol/L;④家族史:患者直系親屬中有患此病者;⑤吸煙史:每天吸煙≥5支并持續1年以上時間;⑥飲酒史為每周攝入乙醇量≥100 g,持續1年以上;⑦體重指數(BMI)異常:BMI≥24為異常。
1.5 統計分析
由臨床研究人員填寫臨床流行病學調查表,數據管理員錄入數據。數據錄入由雙人同時錄入網絡平臺數據管理系統,建立數據庫。研究結束后,由臨床研究人員、數據管理人員、統計分析人員對已建立數據庫在盲態下進行審核,確認研究數據集和統計分析計劃書后對數據庫進行鎖定。數據交由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醫學研究所臨床評價中心,運用SPSS 17.0軟件對危險因素先進行單因素分析(計量資料以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嚴格遵守1975年制定的赫爾辛基宣言(1983年修訂)關于倫理學的要求,并取得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的倫理批件(批件文號:2010KT-001)。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共調查冠心病心絞痛患者1 002例、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患者963例、心腦合病患者982例。
2.2 3種疾病危險因素的基本情況
如表 1所示,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性別、靜息生活方式、BMI、糖尿病、高血壓、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吸煙、飲酒。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的危險因素包括:家族史、高脂血癥。心腦合病中各危險因素的暴露率:高血壓(73.73%)>BMI異常(57.74%)>吸煙史(31.98%)>靜息生活方式(29.23%)>糖尿病(29.12%)>飲酒史(24.24%)>糖尿病合并高血壓(24.13%)>高脂血癥(22.40%)>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19.14%)>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癥(8.25%)>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7.33%)>家族史(7.33%)。
2.3 3種疾病合并危險因素的基本情況
如表 2所示,心腦合病組合并3個及以上危險因素的例數明顯多于單一心病或腦病組(P < 0.01)。糖尿病合并高血壓,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而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癥、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2.4 心腦合病危險因素的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為了篩選出心腦合病的危險因素,對表 1中10項危險因素進行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最后進入模型的變量為年齡[OR=1.711,95%CI(1.441,2.032)]、高血壓[OR=1.666,95%CI(1.407,1.973)]、糖尿病[OR=1.300,95%CI(1.094,1.544)]、BMI異常[OR=1.373,95%CI(1.177,1.603)]、靜息生活方式[OR=1.336,95%CI(1.124,1.587)](表 3)。提示與單一心病或腦病相比,這些因素加重了患合病的風險。
2.5 心腦合病危險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為排除危險因素間相互作用的影響,我們將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出的年齡、高血壓、糖尿病、BMI異常、靜息生活方式運用forward(conditional)法進行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最后進入模型的變量為年齡[OR=1.690,95%CI(1.420,2.012)]、高血壓[OR=1.558,95%CI(1.312,1.850)]、BMI異常[OR=1.356,95%CI(1.158,1.587)]和靜息生活方式[OR=1.319,95%CI(1.107,1.572)](表 4)。這提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與單一心病或腦病相比,高齡、高血壓、BMI異常、靜息生活方式增大了患合病的風險,是心腦合病的獨立危險因素。
3 討論
單因素分析組間比較有顯著差異的危險因素有:年齡、性別、靜息生活方式、BMI異常、糖尿病、高血壓、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吸煙、飲酒以及合并3個及以上危險因素。心腦合病組患者年齡67.92±9.86歲,明顯高于心病組65.75±10.50歲和腦病組64.23±10.96歲。三組年齡均偏大,進一步驗證了年齡是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9-11],因此臨床及科研人員倡導預防疾病的發生要從中青年抓起[12-14]。心腦合病組女性占46.54%,心病組女性占55.49%,腦病組女性占36.45%。目前有研究發現,雌激素能通過多種機制保護心腦血管系統[15-18],因此絕經期前女性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低于男性,但絕經期后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顯著升高。腦病組女性所占比例最小,可能與腦病組年齡相對偏小,女性尚有雌激素分泌有關。心腦合病組(29.23%)有靜息生活方式的患者比例高于心病組(19.16%)和腦病組(28.25%),可能與心腦合病患者年齡偏大、行動不便有關。
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已嚴重影響我國人口健康。肥胖可導致多種疾病的發生,是心腦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心腦合病、心病和腦病BMI異常的患者所占比例較大,分別為57.74%、48.70%、51.09%,提示BMI異常是誘發三病特別是合病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暴露有糖尿病的患者在心腦合病、心病和腦病組中所占比例依次為29.12%、25.85%、22.12%,可見與單一心病或腦病相比,糖尿病與心腦合病的發生關系更為密切。心腦合病組(73.73%)高血壓的暴露率明顯高于心病組(61.28%)和腦病組(64.28%)。如此高的暴露率提示高血壓屬于心腦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因此疾病預防中應高度重視血壓的控制。糖尿病合并高血壓組間比較差異顯著的原因可能為兩危險因素的組間比較均有顯著差異。吸煙、嗜酒等不良習慣是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三組的暴露率也較高,依次為心腦合病31.98%、24.24%,心病26.85%、15.37%,腦病36.97%、28.04%。合并3個及以上危險因素的合病患者比例(75.05%)明顯高于心病組(59.58%)和腦病組(68.95%),提示危險因素的交互作用更容易引發多部位病變、病情復雜的心腦合病。單因素分析組間比較差異不顯著的危險因素有:家族史、高脂血癥、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癥、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心腦合病(7.33%)、心病(7.78%)及腦病(7.68%)家族史的暴露率均不高,說明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疾病譜的重構,遺傳因素對疾病的發生影響越來越小。
家族史三病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可能說明合病的發生并不比心病和腦病更依賴于遺傳因素的作用,而是各種后天獲得性危險因素出現頻率增高和合并出現的概率增大所致。高脂血癥在心腦合病、心病、腦病中的暴露率分別為22.40%、21.16%、20.77%。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原因可能為:三病的病理基礎均為動脈粥樣硬化,高血脂作為共同的關鍵致病因素對各病的發生作用均較大,或血脂指標未細化為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等而掩蓋了差異,或由選擇性偏倚造成。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癥、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在三病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的原因可能是高脂血癥的影響掩蓋了其差異,或者是對三病的致病影響一致。
經單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出年齡、高血壓、BMI異常、靜息生活方式4項獨立的心腦合病危險因素,提示高齡、高血壓、BMI異常、靜息生活方式可單獨作用,增大心腦合病的患病風險。
危險因素有可干預和不可干預之分。年齡、性別、家族史屬于不可干預的危險因素,但大部分危險因素如靜息生活方式、BMI異常、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吸煙、飲酒等屬于可干預的危險因素,是可防可控的。因此,我們提倡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平衡膳食,適當體育活動和體育鍛煉,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保持樂觀愉快的情緒預防危險因素的發生。當可干預的危險因素已發生時,要及時干預,如控制血糖、血壓、血脂水平,適當鍛煉,控制體重,戒煙限酒,以預防心病或腦病的發生;患有心病或腦病時,積極控制危險因素,防止危險因素程度加重或多種危險因素共同作用從而導致原有疾病加重或發展為心腦合病等多病位復雜疾病。
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橫斷面研究方法雖然適用于慢性或少見病的分析,但往往只是新疾病或領域研究的第一步。本橫斷面研究既不能說明這些危險因素是否為心腦合病的病因[19, 20],也不能明確合病是原發病,還是由心病或腦病發展而來。本研究納入的危險因素較少,今后可在本研究基礎上細化血脂等指標,并納入更多可能的危險因素,如社會、心理、經濟等因素[21-31]。亦可嘗試做健康人患心腦合病的風險評估[32, 33]。
本研究通過對比研究心病、腦病的危險因素,探討心腦合病的危險因素,為預防和控制心腦合病的發生提供依據,即未病先防;并通過認識三病的危險因素,來預防由心病或腦病發展為多病位的心腦合病及心腦合病病情惡化,即既病防變。下一步,我們還將研究心腦合病的診斷和治療,為臨床診療的規范化提供依據。
冠心病心絞痛和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同屬于動脈粥樣硬化性疾病[1, 2]。由于致病因素、病理基礎等高度一致,臨床上出現越來越多的同患兩病的患者。上述兩病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給患者帶來了極大的痛苦,給家庭及社會造成了沉重的負擔。針對這一現狀,楊關林教授基于多年臨床實踐及科學研究首次提出“心腦合病”的概念[3, 4]來研究如何預防和治療心腦合病,以降低死亡率和致殘率。目前國內外關于心腦合病的研究報道較少,有關心腦合病危險因素的流行病學分析性研究亦少見,本研究旨在通過與單一心病或腦病危險因素的對比,揭示心腦合病的危險因素,為預防心腦合病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橫斷面調查研究方法。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從我國11家三甲醫院納入符合標準的冠心病心絞痛患者。這11家醫院包括: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遼寧省中醫藥研究院)、遼寧省血栓病中西醫結合醫療中心、大連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撫順市中醫院、丹東市中醫院、營口市中醫院、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盛京醫院)、中國中醫研究院附屬西苑醫院、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沈陽軍區總醫院。
1.2 調查對象的篩選
1.2.1 心腦合病
1.2.1.1 納入標準
①符合冠心病心絞痛,同時符合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2~8周)診斷標準;②年齡在35~85歲;③簽署知情同意書。
1.2.1.2 排除標準
①風濕性心臟病、甲亢性心臟病、心肌炎、心肌病、高心病等非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②心肌梗死,無癥狀性心肌缺血、缺血性心肌病等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③腦栓塞、腦出血、短暫性腦缺血發作、腔隙性腦梗死;④除動脈粥樣硬化以外其他原因所致的腦梗死,如動脈炎、腦腫瘤、腦外傷、腦寄生蟲、代謝障礙、真性紅細胞增多癥、血栓性栓塞、顱內血管畸形、腦淀粉樣變性等。
1.2.1.3 剔除標準
①不符合診斷、納入標準而被誤納入者;②觀察中無任何可利用數據者。
1.2.1.4 診斷標準
不穩定性心絞痛的診斷按中華醫學會2007年公布的《不穩定性心絞痛和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診斷與治療指南》 [5];穩定性心絞痛的診斷按《中國慢性穩定性心絞痛診斷與治療指南》 [6](2007年);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的診斷按1995年中華醫學會制定的《各類腦血管病診斷要點》 [7],并參照《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 [8](2005年)。
1.2.2 冠心病心絞痛
診斷標準、剔除標準、納入標準、排除標準同心腦合病中涉及的冠心病心絞痛的各項標準。
1.2.3 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
診斷標準、剔除標準、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同心腦合病中涉及的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的各項標準。
1.3 調查內容和方法
由經過培訓的臨床研究人員使用統一的流行病學調查表對調查對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包括患者的一般情況(姓名、職業、出生地等)和危險因素(體重、血壓、血脂、血糖等)等。
1.4 危險因素判定標準
對每例患者均進行詳細的病史詢問和仔細的體格檢查、理化檢驗,危險因素按下列標準確定:①高血壓:既往有高血壓史或新診斷的高血壓,采用美國JNCⅦ指南標準,連續2次在靜息狀態下收縮壓(SBP)≥140 mmHg和/或舒張壓(DBP)≥90 mmHg;②糖尿病:既往已確診的糖尿病或新診斷的糖尿病,采用美國糖尿病協會標準診斷,空腹血糖≥7.0 mmol/L和/或餐后2小時血糖≥11.1 mmol/ L;③高脂血癥:既往有明顯的高脂血癥或入院后經生化檢查發現血脂增高,血清總膽固醇(TC)≥5.20 mmol/L或甘油三酯(TG)≥1.70 mmol/L或LDLC≥2.60 mmol/L;④家族史:患者直系親屬中有患此病者;⑤吸煙史:每天吸煙≥5支并持續1年以上時間;⑥飲酒史為每周攝入乙醇量≥100 g,持續1年以上;⑦體重指數(BMI)異常:BMI≥24為異常。
1.5 統計分析
由臨床研究人員填寫臨床流行病學調查表,數據管理員錄入數據。數據錄入由雙人同時錄入網絡平臺數據管理系統,建立數據庫。研究結束后,由臨床研究人員、數據管理人員、統計分析人員對已建立數據庫在盲態下進行審核,確認研究數據集和統計分析計劃書后對數據庫進行鎖定。數據交由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醫學研究所臨床評價中心,運用SPSS 17.0軟件對危險因素先進行單因素分析(計量資料以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嚴格遵守1975年制定的赫爾辛基宣言(1983年修訂)關于倫理學的要求,并取得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的倫理批件(批件文號:2010KT-001)。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共調查冠心病心絞痛患者1 002例、動脈粥樣硬化性血栓性腦梗死患者963例、心腦合病患者982例。
2.2 3種疾病危險因素的基本情況
如表 1所示,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性別、靜息生活方式、BMI、糖尿病、高血壓、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吸煙、飲酒。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的危險因素包括:家族史、高脂血癥。心腦合病中各危險因素的暴露率:高血壓(73.73%)>BMI異常(57.74%)>吸煙史(31.98%)>靜息生活方式(29.23%)>糖尿病(29.12%)>飲酒史(24.24%)>糖尿病合并高血壓(24.13%)>高脂血癥(22.40%)>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19.14%)>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癥(8.25%)>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7.33%)>家族史(7.33%)。
2.3 3種疾病合并危險因素的基本情況
如表 2所示,心腦合病組合并3個及以上危險因素的例數明顯多于單一心病或腦病組(P < 0.01)。糖尿病合并高血壓,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而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癥、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2.4 心腦合病危險因素的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為了篩選出心腦合病的危險因素,對表 1中10項危險因素進行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最后進入模型的變量為年齡[OR=1.711,95%CI(1.441,2.032)]、高血壓[OR=1.666,95%CI(1.407,1.973)]、糖尿病[OR=1.300,95%CI(1.094,1.544)]、BMI異常[OR=1.373,95%CI(1.177,1.603)]、靜息生活方式[OR=1.336,95%CI(1.124,1.587)](表 3)。提示與單一心病或腦病相比,這些因素加重了患合病的風險。
2.5 心腦合病危險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為排除危險因素間相互作用的影響,我們將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出的年齡、高血壓、糖尿病、BMI異常、靜息生活方式運用forward(conditional)法進行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最后進入模型的變量為年齡[OR=1.690,95%CI(1.420,2.012)]、高血壓[OR=1.558,95%CI(1.312,1.850)]、BMI異常[OR=1.356,95%CI(1.158,1.587)]和靜息生活方式[OR=1.319,95%CI(1.107,1.572)](表 4)。這提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與單一心病或腦病相比,高齡、高血壓、BMI異常、靜息生活方式增大了患合病的風險,是心腦合病的獨立危險因素。
3 討論
單因素分析組間比較有顯著差異的危險因素有:年齡、性別、靜息生活方式、BMI異常、糖尿病、高血壓、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吸煙、飲酒以及合并3個及以上危險因素。心腦合病組患者年齡67.92±9.86歲,明顯高于心病組65.75±10.50歲和腦病組64.23±10.96歲。三組年齡均偏大,進一步驗證了年齡是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9-11],因此臨床及科研人員倡導預防疾病的發生要從中青年抓起[12-14]。心腦合病組女性占46.54%,心病組女性占55.49%,腦病組女性占36.45%。目前有研究發現,雌激素能通過多種機制保護心腦血管系統[15-18],因此絕經期前女性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低于男性,但絕經期后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顯著升高。腦病組女性所占比例最小,可能與腦病組年齡相對偏小,女性尚有雌激素分泌有關。心腦合病組(29.23%)有靜息生活方式的患者比例高于心病組(19.16%)和腦病組(28.25%),可能與心腦合病患者年齡偏大、行動不便有關。
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已嚴重影響我國人口健康。肥胖可導致多種疾病的發生,是心腦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心腦合病、心病和腦病BMI異常的患者所占比例較大,分別為57.74%、48.70%、51.09%,提示BMI異常是誘發三病特別是合病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暴露有糖尿病的患者在心腦合病、心病和腦病組中所占比例依次為29.12%、25.85%、22.12%,可見與單一心病或腦病相比,糖尿病與心腦合病的發生關系更為密切。心腦合病組(73.73%)高血壓的暴露率明顯高于心病組(61.28%)和腦病組(64.28%)。如此高的暴露率提示高血壓屬于心腦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因此疾病預防中應高度重視血壓的控制。糖尿病合并高血壓組間比較差異顯著的原因可能為兩危險因素的組間比較均有顯著差異。吸煙、嗜酒等不良習慣是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三組的暴露率也較高,依次為心腦合病31.98%、24.24%,心病26.85%、15.37%,腦病36.97%、28.04%。合并3個及以上危險因素的合病患者比例(75.05%)明顯高于心病組(59.58%)和腦病組(68.95%),提示危險因素的交互作用更容易引發多部位病變、病情復雜的心腦合病。單因素分析組間比較差異不顯著的危險因素有:家族史、高脂血癥、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癥、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心腦合病(7.33%)、心病(7.78%)及腦病(7.68%)家族史的暴露率均不高,說明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疾病譜的重構,遺傳因素對疾病的發生影響越來越小。
家族史三病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可能說明合病的發生并不比心病和腦病更依賴于遺傳因素的作用,而是各種后天獲得性危險因素出現頻率增高和合并出現的概率增大所致。高脂血癥在心腦合病、心病、腦病中的暴露率分別為22.40%、21.16%、20.77%。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原因可能為:三病的病理基礎均為動脈粥樣硬化,高血脂作為共同的關鍵致病因素對各病的發生作用均較大,或血脂指標未細化為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等而掩蓋了差異,或由選擇性偏倚造成。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癥、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糖尿病合并高血壓合并高脂血癥在三病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的原因可能是高脂血癥的影響掩蓋了其差異,或者是對三病的致病影響一致。
經單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出年齡、高血壓、BMI異常、靜息生活方式4項獨立的心腦合病危險因素,提示高齡、高血壓、BMI異常、靜息生活方式可單獨作用,增大心腦合病的患病風險。
危險因素有可干預和不可干預之分。年齡、性別、家族史屬于不可干預的危險因素,但大部分危險因素如靜息生活方式、BMI異常、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吸煙、飲酒等屬于可干預的危險因素,是可防可控的。因此,我們提倡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平衡膳食,適當體育活動和體育鍛煉,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保持樂觀愉快的情緒預防危險因素的發生。當可干預的危險因素已發生時,要及時干預,如控制血糖、血壓、血脂水平,適當鍛煉,控制體重,戒煙限酒,以預防心病或腦病的發生;患有心病或腦病時,積極控制危險因素,防止危險因素程度加重或多種危險因素共同作用從而導致原有疾病加重或發展為心腦合病等多病位復雜疾病。
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橫斷面研究方法雖然適用于慢性或少見病的分析,但往往只是新疾病或領域研究的第一步。本橫斷面研究既不能說明這些危險因素是否為心腦合病的病因[19, 20],也不能明確合病是原發病,還是由心病或腦病發展而來。本研究納入的危險因素較少,今后可在本研究基礎上細化血脂等指標,并納入更多可能的危險因素,如社會、心理、經濟等因素[21-31]。亦可嘗試做健康人患心腦合病的風險評估[32, 33]。
本研究通過對比研究心病、腦病的危險因素,探討心腦合病的危險因素,為預防和控制心腦合病的發生提供依據,即未病先防;并通過認識三病的危險因素,來預防由心病或腦病發展為多病位的心腦合病及心腦合病病情惡化,即既病防變。下一步,我們還將研究心腦合病的診斷和治療,為臨床診療的規范化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