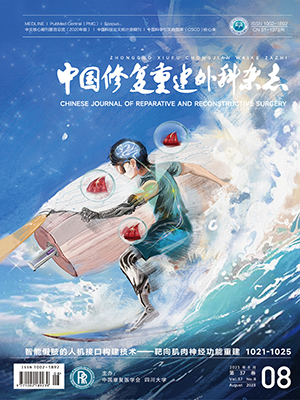肩袖是運動醫學中容易損傷的部位之一,是肩關節重要組成部分,由岡上肌、岡下肌、肩胛下肌和小圓肌及其肌腱組成[1],對維持肩關節的穩定及活動起著重要作用。對肩袖損傷進行積極的醫療干預能有效減輕患者疼痛,改善上肢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損傷的肩袖肌腱具有一定自愈能力,其愈合過程包括炎癥期、增殖期和重塑期3個階段[2]。相關研究報道美國接受肩袖修復的患者數量較10年前增加了2倍[3],而中國尚未實施大規模的肩袖損傷流行病學調查。據推測,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生活方式變化,需要行肩袖治療的患者數量將迅速增加[4]。隨著近年來肩袖治療的發展,各種生物制劑被廣泛應用于肩袖損傷修復的臨床治療,且取得良好效果。目前報道較多的用于治療肩袖損傷的生物制劑包括多種生長因子、富血小板血漿(platelet rich plasma,PRP)、干細胞、外泌體等。本綜述將總結上述生物制劑在肩袖損傷治療中的現狀及未來趨勢,為臨床醫生和患者提供可靠的臨床經驗和治療選擇。
1 PRP
PRP一直是骨科再生醫學研究的焦點,它是一種通過對人全血進行離心而獲得的富含高濃度血小板、白細胞和纖維蛋白的血漿[5],且制備過程較其他生物制品相對容易[5]。由于肩袖損傷后修復愈合過程較長,應用生物因子修復損傷肩袖成為生物強化的主要手段之一。而PRP富含多種生長因子,如PDGF-B、TGF-β1、TGF-β2、IGF-1、VEGF等[6-7],理論上注射PRP是局部輸送生長因子和細胞因子,可能會促進肩袖愈合。以下將從局部PRP注射、PRP聯合關節鏡及PRP與其他生物制劑聯合三方面對肩袖損傷修復進行闡述。
1.1 局部PRP注射
Lana等[8]將PRP分為4類,即純PRP(pure PRP,P-PRP)、富白細胞PRP(leucocyte-rich PRP,LR-PRP)、純富血小板纖維蛋白、富白細胞血小板纖維蛋白。目前,對于局部注射PRP用于臨床前研究和臨床研究治療肩袖損傷的推薦不一。有研究對兔慢性跟腱損傷模型局部注射低白細胞富血小板血漿(leukocyte-poor PRP,LP-PRP)和LR-PRP治療肌腱病的效果進行比較,結果表明LR-PRP有更好的合成代謝作用,LP-PRP刺激炎癥并損害修復過程[9];而在另一項肩袖肌腱修復的臨床研究中,LP-PRP卻比LR-PRP更能促進肌腱細胞增殖[10]。一項臨床前研究制備小鼠急性岡上肌腱損傷模型,用LR-PRP和LP-PRP局部注射治療,結果發現LR-PRP可有效促進肩袖修復后早期骨-肌腱界面愈合,而LP-PRP促進肩袖損傷后期愈合[11]。Peng等[12]的臨床研究報道局部注射LP-PRP能改善關節鏡下肩袖修補術后肩關節運動功能,降低再撕裂率,減少疼痛;而LR-PRP除了可緩解疼痛外,其他方面并未得到顯著改善。Hurley等[13]的綜述報道局部注射PRP能提高肌腱愈合率;還有研究報道局部注射PRP治療部分肩袖撕裂,術后長期隨訪過程中疼痛和肩部功能方面有明顯改善,而在短、中期隨訪中僅在肩部功能方面有所改善[14-15];而無論肩袖撕裂大小如何,局部注射LP-PRP在中、長期隨訪中都能顯著降低術后再撕裂率[16]。Rossi等[17]在肩峰下注射PRP可顯著改善大多數保守治療無效的肩袖撕裂患者肩部功能、疼痛和睡眠障礙,并在平均12個月隨訪中大多數患者恢復了傷前相同運動水平。Moretti等[18]發現PRP一次性注射治療岡上肌腱病是一種有效的保守治療方法,可減輕患者疼痛,提高生活質量和功能評分。
1.2 PRP結合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
Feltri等[19]在肩關節鏡肩袖修復術中使用PRP作為補充物,可顯著降低再撕裂率。Cavendish等[20]證實術中應用PRP降低了肩袖修復失敗風險,并且無論肩袖撕裂大小,修復效果是一致的。Xu等[21]發現PRP組的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顯著改善,再撕裂率顯著降低,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聯合PRP可顯著降低患者的長期再撕裂率和肩部疼痛,改善患者長期肩部功能。Li等[22]在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中使用PRP可以改善疼痛程度和功能結果評分,同時降低術后再撕裂率;另一項類似研究[23]也證實關節鏡下修復肩袖撕裂的PRP治療顯著降低了再撕裂率。Zhang等[24]在術中、術后7 d和14 d重復注射LP-PRP,對減少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后患者再撕裂率和提高Goutallier分級具有積極作用。Pandey等[25]對102例(P-PRP組52例、對照組50例)大型退行性撕裂患者進行關節鏡下單排修復并平均隨訪2年,發現P-PRP可加速肩袖和周圍組織的血管生成,與單純手術組相比,P-PRP組再撕裂率顯著降低。
雖然PRP結合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有較好的臨床修復效果,但尚無明確證據表明PRP結合關節鏡下修復岡上肌撕裂的臨床結果優于單純關節鏡下修復[26]。澳大利亞一個研究小組公布了2項P-PRP陰性結果的隨機對照試驗,比較使用和不使用P-PRP的關節鏡下岡上肌修復術患者短、中期臨床和放射學結果。在這2項研究中,術后7、14 d分別在肌腱修復部位應用了2種劑量P-PRP,在短期(16周)內發現使用P-PRP并未改善早期功能恢復、活動度和力量[27];在中期(36~51個月)發現使用P-PRP只在無痛外展強度上有益,而基于MRI的肌腱質量或再撕裂率無明顯差異,由于肌腱質量和再撕裂率是主要結果,因此這2項研究結論是使用P-PRP增強并不能產生更穩固的肌腱修復[28]。
1.3 PRP與其他生物制劑聯合
有研究[29]使用皮質類固醇與LP-PRP注射治療崗上肌撕裂,1個月后部分岡上肌撕裂患者疼痛減輕和功能改善相似,隨訪6個月PRP治療效果優于皮質類固醇。Cai等[30]將透明質酸鈉和PRP聯合使用治療中小型肩袖撕裂,發現PRP組和透明質酸鈉+PRP組撕裂大小均明顯減小,以透明質酸鈉+PRP組更明顯。Kwong等[31]在超聲引導下注射皮質類固醇和PRP治療后,短期隨訪時患者疼痛和功能均有明顯改善,長期隨訪中PRP與皮質類固醇相比并無更多優勢。Bao等[32]在PRP凝膠中加入氧化石墨烯,改善了PRP凝膠的機械性能,并促進肩袖再生,PRP和氧化石墨烯結合在肩袖損傷治療中具有很大發展潛力。
綜上,在肌肉骨骼疾病治療實踐中,盡管PRP在基礎和臨床研究方面都顯示出較好療效,但迄今為止對PRP仍然缺乏肩袖損傷治療國際標準化[33]。目前關于肩袖損傷和肌腱病的PRP治療研究結果不一,也無證據表明肩袖損傷治療中應用PRP在改善功能結果方面的優越性[34-38]。因此,未來PRP的臨床應用還需進一步探索。
2 生長因子
生長因子是由炎癥細胞、血小板和成纖維細胞產生的參與控制細胞生長和分化的信號分子,在炎癥的不同階段均活躍。動物和臨床研究均顯示,局部應用細胞因子可促進肩袖損傷修復,肩袖損傷后的愈合過程包括炎癥反應期、修復期和重塑期,修復期內的PDGF、TGF-β、bFGF、IGF-1和VEGF等因子可使細胞增殖和基質分泌,從而促進肩袖損傷修復[39-41]。
2.1 PDGF
PDGF是能調節細胞增殖和分化的生長因子之一,可調節損傷部位蛋白質和DNA合成,調節其他生長因子表達,降低IL-1、IL-6等促炎細胞因子的mRNA水平,增加IL-4、IL-10和IL-13等抗炎細胞因子mRNA水平。因此,有研究[42]表明PDGF有潛力通過抑制炎癥反應來促進肩袖肌腱炎的肌腱愈合。Wang等[43]研究證實PDGF可以促進肩袖損傷修復后的腱-骨愈合,有促進肩袖損傷治療的潛力。PDGF還可與IGF-1和TGF-β等多種生長因子聯合應用,對肌腱細胞的增殖和遷移有促進作用,以促進肌腱愈合和肩袖修復[44-45]。
2.2 bFGF
bFGF能促進成纖維細胞合成膠原蛋白,在體外可促進肩袖肌腱細胞的增殖和膠原分泌,體內可增強肌腱愈合強度、促進腱-骨重塑。Kataoka等[46]的研究表明bFGF聯合PRP治療可促進肌腱端血管生成、肌腱成熟和纖維軟骨再生,提高肌腱的機械強度,促進肌腱和腱-骨交界處愈合,二者可能具有協同作用。
2.3 TGF-β
TGF-β可調節細胞遷移和蛋白水解酶表達,具有纖維連接蛋白結合作用,可終止細胞增殖和刺激膠原生成[47]。TGF-β主要有TGF-β1、TGF-β2和TGF-β3 3個亞型。有研究發現在肩袖修復過程中TGF-β1和TGF-β2濃度顯著增加[48];故采用含TGF-β1的縫線來修復肩袖,能持續、安全地釋放TGF-β1促進肩袖愈合[49]。3個亞型中,TGF-β3最有潛力改善肩袖修復部位的局部微環境,研究者在大鼠體內用含TGF-β3 的支架構建腱-骨結構,結果顯示有較好的生物力學性能[50]。Kovacevic等[51]將TGF-β3用一種可注射的鈣-磷酸鹽基質輸送至岡上肌肌腱-骨表面進行肩袖修復,促進新骨形成,改善腱-骨界面膠原結構;在術后4周加入TGF-β3可顯著提高修復強度。另外,TGF-β1、IGF-1和甲狀旁腺激素聯合使用可促進肌腱細胞增殖和分化,改善修復的腱-骨界面生物力學和組織學質量[52]。
2.4 IGF-1
IGF-1可促進細胞增殖和遷移,刺激基質生成[47]。IGF-1在肩袖損傷愈合過程的不同階段都是活躍的。其在炎癥早期高表達,使肌腱成纖維細胞產生膠原[53],可促進成纖維細胞的細胞增殖和遷移[47,54]。研究者發現,IGF-1與PDGF-BB在促進膠原蛋白產生和細胞增殖方面可以發揮協同作用[55]。Dahlgren等[56]認為IGF-1治療肌腱炎有潛在作用,由于IGF-1可影響巨噬細胞極化,從而間接影響肩袖修復。因此,IGF-1在未來的應用潛力可能集中在肌腱愈合過程中的炎癥階段。雖然IGF-1廣泛用于基礎研究,但其是一種外源性生長因子,目前還未獲批準用于臨床。
2.5 VEGF
VEGF是最早從腫瘤液中提純出來并能影響血管生成活性的生長因子[57],有多種亞型包括VEGF-A、VEGF-B、VEGF-C、VEGF-D、VEGF-E等[58]。在炎癥階段之后發生血管化時,VEGF受體表達高度增加[59]。據報道,VEGF主要通過影響血管生成來促進肌腱愈合[60]。目前仍無證據表明VEGF可在不造成任何損害情況下顯著改善肩袖修復,在其廣泛應用于肩袖損傷修復之前,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來證明VEGF是否有利于肌腱愈合過程。
綜上,在肩袖撕裂的臨床治療中,多種生長因子聯合應用可能是一種較好選擇。另外,由于原位肌腱細胞數量較少,使用生長因子刺激細胞增殖的效果有限,仍需要進行更多體內研究來發現這些生長因子的潛力。因此,研究者試圖引入外來細胞,特別是干細胞修復肌腱,并取得了一些滿意結果[61-62]。
3 干細胞
干細胞是一種能增殖、再生、具有自我更新和復制潛能的未分化細胞,能在特定條件下分化為各種類型成體細胞。最常見的干細胞來源是胚胎干細胞和成體干細胞,因倫理相關限制,肩袖損傷修復主要研究成體干細胞,主要來源有BMSCs、脂肪來源干細胞(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ADSCs)[63-64]、肌腱來源干細胞(tendon-derived stem cells,TDSCs)[65]和臍帶血來源干細胞(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stem cells,UCBSCs)[66-67]等。干細胞在肌腱愈合過程中對炎癥和血管生成起著重要調節作用,刺激了纖維軟骨形成、膠原沉積,提高了肩袖的生物力學強度。
3.1 BMSCs
BMSCs是促進肩袖修復最容易獲得的干細胞來源之一,可從患者自體髂骨嵴和肱骨近端獲得,并應用于腱-骨愈合。有研究利用BMSCs修復無胸腺大鼠受損的肩袖肌腱,結果顯示術后2周BMSCs組受損肌腱的組織學形態和力學性能較對照組有明顯改善[68]。Hao等[69]發現負載辛伐他汀的絲素膜具有較好的生物相容性,體外實驗證實其能促進BMSCs增殖和成骨分化;體內實驗也表明其能促進腱-骨愈合,減輕慢性肩袖損傷的炎癥反應。另一項研究[70]證實了3D打印聚乳酸-羥基乙酸支架與BMSCs聯合使用,可促進兔肩袖修復模型的腱-骨愈合。
3.2 ADSCs
ADSCs主要優勢是可以從脂肪組織中大量提取,同時其增殖能力強于BMSCs[71],可能在生長因子和機械應力作用下分化為肌腱細胞[72]。Chen等[73]發現注射人ADSCs的炎癥細胞數量明顯減少,肌腱纖維排列和肌腱組織也得到改善,局部應用人ADSCs有可能恢復肌腱的抗張強度。Lipner等[74]報道ADSCs可以逆轉急性腱-骨愈合中占主導地位的纖維血管瘢痕反應,促進急性肩袖損傷修復。另外,移植到受傷部位的ADSCs可以增加肱骨近端骨密度,以促進腱-骨愈合,修復慢性撕裂[75]。Song等[76]發現凍存ADSCs片是一種具有較高臨床應用潛力的支架,能有效促進肩袖腱-骨愈合。
3.3 TDSCs
TDSCs是近年來研究者發現的一種新的細胞類型,它可以在體內、外研究中再生肌腱樣組織,這一發現為肩袖修復帶來了新的選擇[77]。目前已成功從肩袖組織中分離出TDSCs,并證實了這種新型干細胞用于細胞治療的潛在用途[78]。然而肌腱細胞或TDSCs并不是促進肌腱修復的最佳細胞來源,主要是原因是TDSCs濃度相對較低,細胞增殖速度較慢,臨床應用相對困難[79];另外,在TDSCs體外培養過程中,細胞會逐漸失去表型,增加Ⅲ型膠原合成比例。
3.4 UCBSCs
UCBSCs具有高分化潛能并且在出生后容易收集和擴增,是臨床上同種異體移植的理想選擇[80]。相對于BMSCs和ADSCs,UCBSCs的培養時間最長,增殖能力最強[81]。臨床前研究表明,UCBSCs對肩袖損傷后肌腱修復有治療作用。例如,在超聲引導下向慢性兔全層肩袖肌腱撕裂模型注射UCBSCs后,與其他組相比,在新生Ⅰ型膠原纖維、細胞增殖活性和血管生成方面有明顯改善[82]。然而,另一項為期2年的UCBSCs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試驗顯示,與對照組相比,沒有出現與治療相關的不良反應,但在加強肌腱移植介導的愈合方面也無改善[83]。因此,需要進一步臨床研究來驗證UCBSCs對肩袖損傷的療效。
綜上,來源相對廣泛的BMSCs和ADSCs仍是促進肌腱修復的外源細胞首選。關于干細胞在肩部手術中應用的臨床研究非常有限,目前已在動物模型中進行了大量干細胞應用研究,但其應用于臨床肩袖損傷修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進一步研究。
4 外泌體
外泌體是一類細胞外囊泡,由多種類型細胞釋放,存在于體液和細胞培養上清液中。也有研究報道循環外泌體通過上調肌腱和腱-骨相關標記物表達來促進腱細胞增殖和遷移[84]。外泌體是體內不同細胞間的重要信使,Yao等[85]發現蛋白質、miRNA、mRNA和脂質是外泌體的主要成分,通過離心或分離試劑盒提取MSCs的外泌體來修復肌腱,外泌體中相關的miRNA和蛋白質對肌腱細胞有重要影響。此外,Lan等[86]證明M2巨噬細胞衍生的外泌體可修復肩袖損傷,因其含有許多刺激肩袖愈合過程的重要蛋白質和miRNA。Leong等[87]利用分離的ADSCs外泌體來調節肩袖肌,發現可以延緩肩袖肌的萎縮和退變。而TGF-β1修飾的BMSCs來源外泌體的miR-29a通過靶向FABP3促進肌腱細胞的增殖、遷移和纖維化[88]。ADSCs來源外泌體介導的M1/M2巨噬細胞極化平衡有助于改善慢性肩袖損傷肌腱病,表明調節M1/M2巨噬細胞極化平衡可能成為慢性肩袖損傷肌腱病治療的新靶點[89]。因此,在未來外泌體也是外科醫生肩袖修復方法的重要選擇之一。
5 小結及展望
利益沖突 在課題研究和文章撰寫過程中不存在利益沖突;經費支持沒有影響文章觀點及其報道
作者貢獻聲明 尹正勃:綜述構思及設計、文章撰寫、資料收集;陳志安、朱弈霏、尹妮、張必歡:對文章修改提出建設性意見及資料收集;徐永清、周田華、譚洪波:審閱文章并參與觀點形成
肩袖是運動醫學中容易損傷的部位之一,是肩關節重要組成部分,由岡上肌、岡下肌、肩胛下肌和小圓肌及其肌腱組成[1],對維持肩關節的穩定及活動起著重要作用。對肩袖損傷進行積極的醫療干預能有效減輕患者疼痛,改善上肢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損傷的肩袖肌腱具有一定自愈能力,其愈合過程包括炎癥期、增殖期和重塑期3個階段[2]。相關研究報道美國接受肩袖修復的患者數量較10年前增加了2倍[3],而中國尚未實施大規模的肩袖損傷流行病學調查。據推測,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生活方式變化,需要行肩袖治療的患者數量將迅速增加[4]。隨著近年來肩袖治療的發展,各種生物制劑被廣泛應用于肩袖損傷修復的臨床治療,且取得良好效果。目前報道較多的用于治療肩袖損傷的生物制劑包括多種生長因子、富血小板血漿(platelet rich plasma,PRP)、干細胞、外泌體等。本綜述將總結上述生物制劑在肩袖損傷治療中的現狀及未來趨勢,為臨床醫生和患者提供可靠的臨床經驗和治療選擇。
1 PRP
PRP一直是骨科再生醫學研究的焦點,它是一種通過對人全血進行離心而獲得的富含高濃度血小板、白細胞和纖維蛋白的血漿[5],且制備過程較其他生物制品相對容易[5]。由于肩袖損傷后修復愈合過程較長,應用生物因子修復損傷肩袖成為生物強化的主要手段之一。而PRP富含多種生長因子,如PDGF-B、TGF-β1、TGF-β2、IGF-1、VEGF等[6-7],理論上注射PRP是局部輸送生長因子和細胞因子,可能會促進肩袖愈合。以下將從局部PRP注射、PRP聯合關節鏡及PRP與其他生物制劑聯合三方面對肩袖損傷修復進行闡述。
1.1 局部PRP注射
Lana等[8]將PRP分為4類,即純PRP(pure PRP,P-PRP)、富白細胞PRP(leucocyte-rich PRP,LR-PRP)、純富血小板纖維蛋白、富白細胞血小板纖維蛋白。目前,對于局部注射PRP用于臨床前研究和臨床研究治療肩袖損傷的推薦不一。有研究對兔慢性跟腱損傷模型局部注射低白細胞富血小板血漿(leukocyte-poor PRP,LP-PRP)和LR-PRP治療肌腱病的效果進行比較,結果表明LR-PRP有更好的合成代謝作用,LP-PRP刺激炎癥并損害修復過程[9];而在另一項肩袖肌腱修復的臨床研究中,LP-PRP卻比LR-PRP更能促進肌腱細胞增殖[10]。一項臨床前研究制備小鼠急性岡上肌腱損傷模型,用LR-PRP和LP-PRP局部注射治療,結果發現LR-PRP可有效促進肩袖修復后早期骨-肌腱界面愈合,而LP-PRP促進肩袖損傷后期愈合[11]。Peng等[12]的臨床研究報道局部注射LP-PRP能改善關節鏡下肩袖修補術后肩關節運動功能,降低再撕裂率,減少疼痛;而LR-PRP除了可緩解疼痛外,其他方面并未得到顯著改善。Hurley等[13]的綜述報道局部注射PRP能提高肌腱愈合率;還有研究報道局部注射PRP治療部分肩袖撕裂,術后長期隨訪過程中疼痛和肩部功能方面有明顯改善,而在短、中期隨訪中僅在肩部功能方面有所改善[14-15];而無論肩袖撕裂大小如何,局部注射LP-PRP在中、長期隨訪中都能顯著降低術后再撕裂率[16]。Rossi等[17]在肩峰下注射PRP可顯著改善大多數保守治療無效的肩袖撕裂患者肩部功能、疼痛和睡眠障礙,并在平均12個月隨訪中大多數患者恢復了傷前相同運動水平。Moretti等[18]發現PRP一次性注射治療岡上肌腱病是一種有效的保守治療方法,可減輕患者疼痛,提高生活質量和功能評分。
1.2 PRP結合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
Feltri等[19]在肩關節鏡肩袖修復術中使用PRP作為補充物,可顯著降低再撕裂率。Cavendish等[20]證實術中應用PRP降低了肩袖修復失敗風險,并且無論肩袖撕裂大小,修復效果是一致的。Xu等[21]發現PRP組的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顯著改善,再撕裂率顯著降低,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聯合PRP可顯著降低患者的長期再撕裂率和肩部疼痛,改善患者長期肩部功能。Li等[22]在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中使用PRP可以改善疼痛程度和功能結果評分,同時降低術后再撕裂率;另一項類似研究[23]也證實關節鏡下修復肩袖撕裂的PRP治療顯著降低了再撕裂率。Zhang等[24]在術中、術后7 d和14 d重復注射LP-PRP,對減少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后患者再撕裂率和提高Goutallier分級具有積極作用。Pandey等[25]對102例(P-PRP組52例、對照組50例)大型退行性撕裂患者進行關節鏡下單排修復并平均隨訪2年,發現P-PRP可加速肩袖和周圍組織的血管生成,與單純手術組相比,P-PRP組再撕裂率顯著降低。
雖然PRP結合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有較好的臨床修復效果,但尚無明確證據表明PRP結合關節鏡下修復岡上肌撕裂的臨床結果優于單純關節鏡下修復[26]。澳大利亞一個研究小組公布了2項P-PRP陰性結果的隨機對照試驗,比較使用和不使用P-PRP的關節鏡下岡上肌修復術患者短、中期臨床和放射學結果。在這2項研究中,術后7、14 d分別在肌腱修復部位應用了2種劑量P-PRP,在短期(16周)內發現使用P-PRP并未改善早期功能恢復、活動度和力量[27];在中期(36~51個月)發現使用P-PRP只在無痛外展強度上有益,而基于MRI的肌腱質量或再撕裂率無明顯差異,由于肌腱質量和再撕裂率是主要結果,因此這2項研究結論是使用P-PRP增強并不能產生更穩固的肌腱修復[28]。
1.3 PRP與其他生物制劑聯合
有研究[29]使用皮質類固醇與LP-PRP注射治療崗上肌撕裂,1個月后部分岡上肌撕裂患者疼痛減輕和功能改善相似,隨訪6個月PRP治療效果優于皮質類固醇。Cai等[30]將透明質酸鈉和PRP聯合使用治療中小型肩袖撕裂,發現PRP組和透明質酸鈉+PRP組撕裂大小均明顯減小,以透明質酸鈉+PRP組更明顯。Kwong等[31]在超聲引導下注射皮質類固醇和PRP治療后,短期隨訪時患者疼痛和功能均有明顯改善,長期隨訪中PRP與皮質類固醇相比并無更多優勢。Bao等[32]在PRP凝膠中加入氧化石墨烯,改善了PRP凝膠的機械性能,并促進肩袖再生,PRP和氧化石墨烯結合在肩袖損傷治療中具有很大發展潛力。
綜上,在肌肉骨骼疾病治療實踐中,盡管PRP在基礎和臨床研究方面都顯示出較好療效,但迄今為止對PRP仍然缺乏肩袖損傷治療國際標準化[33]。目前關于肩袖損傷和肌腱病的PRP治療研究結果不一,也無證據表明肩袖損傷治療中應用PRP在改善功能結果方面的優越性[34-38]。因此,未來PRP的臨床應用還需進一步探索。
2 生長因子
生長因子是由炎癥細胞、血小板和成纖維細胞產生的參與控制細胞生長和分化的信號分子,在炎癥的不同階段均活躍。動物和臨床研究均顯示,局部應用細胞因子可促進肩袖損傷修復,肩袖損傷后的愈合過程包括炎癥反應期、修復期和重塑期,修復期內的PDGF、TGF-β、bFGF、IGF-1和VEGF等因子可使細胞增殖和基質分泌,從而促進肩袖損傷修復[39-41]。
2.1 PDGF
PDGF是能調節細胞增殖和分化的生長因子之一,可調節損傷部位蛋白質和DNA合成,調節其他生長因子表達,降低IL-1、IL-6等促炎細胞因子的mRNA水平,增加IL-4、IL-10和IL-13等抗炎細胞因子mRNA水平。因此,有研究[42]表明PDGF有潛力通過抑制炎癥反應來促進肩袖肌腱炎的肌腱愈合。Wang等[43]研究證實PDGF可以促進肩袖損傷修復后的腱-骨愈合,有促進肩袖損傷治療的潛力。PDGF還可與IGF-1和TGF-β等多種生長因子聯合應用,對肌腱細胞的增殖和遷移有促進作用,以促進肌腱愈合和肩袖修復[44-45]。
2.2 bFGF
bFGF能促進成纖維細胞合成膠原蛋白,在體外可促進肩袖肌腱細胞的增殖和膠原分泌,體內可增強肌腱愈合強度、促進腱-骨重塑。Kataoka等[46]的研究表明bFGF聯合PRP治療可促進肌腱端血管生成、肌腱成熟和纖維軟骨再生,提高肌腱的機械強度,促進肌腱和腱-骨交界處愈合,二者可能具有協同作用。
2.3 TGF-β
TGF-β可調節細胞遷移和蛋白水解酶表達,具有纖維連接蛋白結合作用,可終止細胞增殖和刺激膠原生成[47]。TGF-β主要有TGF-β1、TGF-β2和TGF-β3 3個亞型。有研究發現在肩袖修復過程中TGF-β1和TGF-β2濃度顯著增加[48];故采用含TGF-β1的縫線來修復肩袖,能持續、安全地釋放TGF-β1促進肩袖愈合[49]。3個亞型中,TGF-β3最有潛力改善肩袖修復部位的局部微環境,研究者在大鼠體內用含TGF-β3 的支架構建腱-骨結構,結果顯示有較好的生物力學性能[50]。Kovacevic等[51]將TGF-β3用一種可注射的鈣-磷酸鹽基質輸送至岡上肌肌腱-骨表面進行肩袖修復,促進新骨形成,改善腱-骨界面膠原結構;在術后4周加入TGF-β3可顯著提高修復強度。另外,TGF-β1、IGF-1和甲狀旁腺激素聯合使用可促進肌腱細胞增殖和分化,改善修復的腱-骨界面生物力學和組織學質量[52]。
2.4 IGF-1
IGF-1可促進細胞增殖和遷移,刺激基質生成[47]。IGF-1在肩袖損傷愈合過程的不同階段都是活躍的。其在炎癥早期高表達,使肌腱成纖維細胞產生膠原[53],可促進成纖維細胞的細胞增殖和遷移[47,54]。研究者發現,IGF-1與PDGF-BB在促進膠原蛋白產生和細胞增殖方面可以發揮協同作用[55]。Dahlgren等[56]認為IGF-1治療肌腱炎有潛在作用,由于IGF-1可影響巨噬細胞極化,從而間接影響肩袖修復。因此,IGF-1在未來的應用潛力可能集中在肌腱愈合過程中的炎癥階段。雖然IGF-1廣泛用于基礎研究,但其是一種外源性生長因子,目前還未獲批準用于臨床。
2.5 VEGF
VEGF是最早從腫瘤液中提純出來并能影響血管生成活性的生長因子[57],有多種亞型包括VEGF-A、VEGF-B、VEGF-C、VEGF-D、VEGF-E等[58]。在炎癥階段之后發生血管化時,VEGF受體表達高度增加[59]。據報道,VEGF主要通過影響血管生成來促進肌腱愈合[60]。目前仍無證據表明VEGF可在不造成任何損害情況下顯著改善肩袖修復,在其廣泛應用于肩袖損傷修復之前,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來證明VEGF是否有利于肌腱愈合過程。
綜上,在肩袖撕裂的臨床治療中,多種生長因子聯合應用可能是一種較好選擇。另外,由于原位肌腱細胞數量較少,使用生長因子刺激細胞增殖的效果有限,仍需要進行更多體內研究來發現這些生長因子的潛力。因此,研究者試圖引入外來細胞,特別是干細胞修復肌腱,并取得了一些滿意結果[61-62]。
3 干細胞
干細胞是一種能增殖、再生、具有自我更新和復制潛能的未分化細胞,能在特定條件下分化為各種類型成體細胞。最常見的干細胞來源是胚胎干細胞和成體干細胞,因倫理相關限制,肩袖損傷修復主要研究成體干細胞,主要來源有BMSCs、脂肪來源干細胞(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ADSCs)[63-64]、肌腱來源干細胞(tendon-derived stem cells,TDSCs)[65]和臍帶血來源干細胞(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stem cells,UCBSCs)[66-67]等。干細胞在肌腱愈合過程中對炎癥和血管生成起著重要調節作用,刺激了纖維軟骨形成、膠原沉積,提高了肩袖的生物力學強度。
3.1 BMSCs
BMSCs是促進肩袖修復最容易獲得的干細胞來源之一,可從患者自體髂骨嵴和肱骨近端獲得,并應用于腱-骨愈合。有研究利用BMSCs修復無胸腺大鼠受損的肩袖肌腱,結果顯示術后2周BMSCs組受損肌腱的組織學形態和力學性能較對照組有明顯改善[68]。Hao等[69]發現負載辛伐他汀的絲素膜具有較好的生物相容性,體外實驗證實其能促進BMSCs增殖和成骨分化;體內實驗也表明其能促進腱-骨愈合,減輕慢性肩袖損傷的炎癥反應。另一項研究[70]證實了3D打印聚乳酸-羥基乙酸支架與BMSCs聯合使用,可促進兔肩袖修復模型的腱-骨愈合。
3.2 ADSCs
ADSCs主要優勢是可以從脂肪組織中大量提取,同時其增殖能力強于BMSCs[71],可能在生長因子和機械應力作用下分化為肌腱細胞[72]。Chen等[73]發現注射人ADSCs的炎癥細胞數量明顯減少,肌腱纖維排列和肌腱組織也得到改善,局部應用人ADSCs有可能恢復肌腱的抗張強度。Lipner等[74]報道ADSCs可以逆轉急性腱-骨愈合中占主導地位的纖維血管瘢痕反應,促進急性肩袖損傷修復。另外,移植到受傷部位的ADSCs可以增加肱骨近端骨密度,以促進腱-骨愈合,修復慢性撕裂[75]。Song等[76]發現凍存ADSCs片是一種具有較高臨床應用潛力的支架,能有效促進肩袖腱-骨愈合。
3.3 TDSCs
TDSCs是近年來研究者發現的一種新的細胞類型,它可以在體內、外研究中再生肌腱樣組織,這一發現為肩袖修復帶來了新的選擇[77]。目前已成功從肩袖組織中分離出TDSCs,并證實了這種新型干細胞用于細胞治療的潛在用途[78]。然而肌腱細胞或TDSCs并不是促進肌腱修復的最佳細胞來源,主要是原因是TDSCs濃度相對較低,細胞增殖速度較慢,臨床應用相對困難[79];另外,在TDSCs體外培養過程中,細胞會逐漸失去表型,增加Ⅲ型膠原合成比例。
3.4 UCBSCs
UCBSCs具有高分化潛能并且在出生后容易收集和擴增,是臨床上同種異體移植的理想選擇[80]。相對于BMSCs和ADSCs,UCBSCs的培養時間最長,增殖能力最強[81]。臨床前研究表明,UCBSCs對肩袖損傷后肌腱修復有治療作用。例如,在超聲引導下向慢性兔全層肩袖肌腱撕裂模型注射UCBSCs后,與其他組相比,在新生Ⅰ型膠原纖維、細胞增殖活性和血管生成方面有明顯改善[82]。然而,另一項為期2年的UCBSCs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試驗顯示,與對照組相比,沒有出現與治療相關的不良反應,但在加強肌腱移植介導的愈合方面也無改善[83]。因此,需要進一步臨床研究來驗證UCBSCs對肩袖損傷的療效。
綜上,來源相對廣泛的BMSCs和ADSCs仍是促進肌腱修復的外源細胞首選。關于干細胞在肩部手術中應用的臨床研究非常有限,目前已在動物模型中進行了大量干細胞應用研究,但其應用于臨床肩袖損傷修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進一步研究。
4 外泌體
外泌體是一類細胞外囊泡,由多種類型細胞釋放,存在于體液和細胞培養上清液中。也有研究報道循環外泌體通過上調肌腱和腱-骨相關標記物表達來促進腱細胞增殖和遷移[84]。外泌體是體內不同細胞間的重要信使,Yao等[85]發現蛋白質、miRNA、mRNA和脂質是外泌體的主要成分,通過離心或分離試劑盒提取MSCs的外泌體來修復肌腱,外泌體中相關的miRNA和蛋白質對肌腱細胞有重要影響。此外,Lan等[86]證明M2巨噬細胞衍生的外泌體可修復肩袖損傷,因其含有許多刺激肩袖愈合過程的重要蛋白質和miRNA。Leong等[87]利用分離的ADSCs外泌體來調節肩袖肌,發現可以延緩肩袖肌的萎縮和退變。而TGF-β1修飾的BMSCs來源外泌體的miR-29a通過靶向FABP3促進肌腱細胞的增殖、遷移和纖維化[88]。ADSCs來源外泌體介導的M1/M2巨噬細胞極化平衡有助于改善慢性肩袖損傷肌腱病,表明調節M1/M2巨噬細胞極化平衡可能成為慢性肩袖損傷肌腱病治療的新靶點[89]。因此,在未來外泌體也是外科醫生肩袖修復方法的重要選擇之一。
5 小結及展望
利益沖突 在課題研究和文章撰寫過程中不存在利益沖突;經費支持沒有影響文章觀點及其報道
作者貢獻聲明 尹正勃:綜述構思及設計、文章撰寫、資料收集;陳志安、朱弈霏、尹妮、張必歡:對文章修改提出建設性意見及資料收集;徐永清、周田華、譚洪波:審閱文章并參與觀點形成